2006年3月,北京举行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耕地不断减少,农业综合能力不强,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放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困难和问题的第一位。
4月,位于中国东北角的北大荒农场开始春播。这也许是全国范畴内春播时间最迟的地域。然而,在上世纪末,北大荒农垦系统粮食总产已经达到100亿斤,提供商品粮70亿斤,这个数字的具体解读是:在满足中国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粮食需求后还绰绰有余。
到2007年,北大荒农场将走过整整60年的长途。今天,我们关注这片漠漠黑土,不只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更是因为我们有责任真实地记录,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卓越努力。
伟大和艰辛同在,辉煌和沉重共存,是军民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周刊特派记者奔赴北大荒采访,为的是向历史敬礼,更是为了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把握今天,赢得未来。
1952年夏天,郑加真奉调回国,至某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报到。1958年3月,上尉军官郑加真与各军兵种的复转军人,乘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东北黑龙江密山小城。自此,郑加真开始了将近50年的北大荒垦荒生涯。
郑加真和一部北大荒农垦史
郑加真非常诚挚地说道,一个人的现实路程会很奇怪,我这个上海人最终参予完成的一部史志,却是北大荒农垦史。
百年复旦学子归来
77岁的郑加真的卧室兼书房,很是狭小,书橱、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其间没有一丝空隙。大卧室就在旁边,但为不打扰老爱人的休息,也是为了不受打扰,这间屋子成为了过日子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的郑加真的“一统小楼”。墙上挂着一幅字:移民书屋。
2005年10月以后,从上海回到哈尔滨的郑加真,这位老移民的床头多了一样装饰物,那是两张胸牌。胸牌上一行小字: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两个大字是:校友。郑加真告诉我,我是真校友,老爱人陪着我一起到上海参加校庆的,以便通行,所以复旦大学多给了一张,郑加真开玩笑说:“我是上世纪1949年被复旦大学录取的,我老爱人是2005年被录取的。”
郑加真生于温州,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到上海谋生,在四川路的邮政总局上班。仅有5岁的郑加真跟着来到沪上。1949年,郑加真成为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录取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郑加真应征入伍。年近半百的父亲来到复旦大学,找到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父亲跟郭先生说,“我就这么一个独养儿子”。而郭先生能够说的,是“国家号召应当支持”。
当年1月,复旦、同济、交大等院校的2000多名上海大学生,脱下便服,穿上军装。经过短暂培训,郑加真于7月入朝,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工作。1952年夏天,郑加真奉调回国,至某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报到。1958年3月,上尉军官郑加真与各军兵种的复转军人,乘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东北黑龙江密山小城。自此,郑加真开始了将近50年的北大荒垦荒生涯。
十年浩劫期间,郑加真“官拜”农业生产连队副连长。浩劫结束,复旦“解放牌”大学生、部队复转军人、老资格移民的郑加真,任职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宣传部副部长、黑龙江农垦史办公室主任。如今,退休的郑加真,所有官衔都已卸下,只一个与写作有关的“衔”还扛着: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郑加真感慨,回到复旦,当年中文系的老先生都不在了,郭绍虞、冯雪峰、唐弢、刘大杰、靳以、方令孺、许杰等等,都不在了;1949年一个班级的老同学,见面的连我就三个人,另外两个是女同学,都是留在复旦当了老师的,“我上前招呼,她们立即认出了是我”。
郑加真非常诚挚地说道,我5岁来上海,到20岁参军入朝,我最富有书生意气的青春年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我是上海人,我对上海有深厚的感情。“只是,一个人的现实路程会很奇怪,我这个上海人最终参与完成的一部史志,却是北大荒农垦史。”
军事博物馆里的“空白”
郑加真说,很多中央领导都曾到过北大荒。邓小平同志来过北大荒垦区,并在丰收的大田里留影;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领导同志来过农垦总局,视察指导工作。温家宝也曾到垦区视察。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垦区工作的时候曾说:我们国家需要稳定的商品粮基地。黑龙江农垦总局始终奋发努力,积极地实现了这样一个“国家级目标”。郑加真说道,“我给你一个概念,在上世纪末,黑龙江农垦总局粮食总产达到100亿斤,提供商品粮70亿斤;这个概念的具体解读是:它在满足中国四个直辖市京、津、沪、渝粮食需求后还绰绰有余。”
在中国的农垦史上,1958年的“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既是一个至今震耳欲聋的宣传名词,更是一个永远名副其实的宏大事件。从最简略的思考出发,这样重大的历史史实,这样重大史实的参与者,以至实际组织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旧健在,至今仍然生活在北大荒农场的现实,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具体到军史和农业史上,都应该为此凿刻下浓重的笔墨。
1988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史志办主任郑加真来到了北京。在郑加真后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移民录》这部书里,他作了这样的记录:
1988年,十万官兵进军北大荒30周年前夕,作者走访了颇有权威的军事博物馆。在一间敞亮的工作室里,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现役军人接待了我。我递上介绍信,并告知来意:作为黑龙江垦区的一名史志工作者,想查阅一下当年转业官兵来北大荒时的部队历史资料。这位军人转身进屋查了好久,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份资料,对我说:“只有这一份,旁的没有了。”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1959年全国烈军属和残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资料,我说道:“这份资料,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想查阅其他资料,特别是十万官兵转业北大荒的资料。”
这位军人歉意地摇了摇头,一再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资料了。
我扫兴而归,想不到偌大的博物馆,竟找不出第二份有关转业官兵的资料了。这就表明: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在军史上仍然是一块“空白”。
59岁的郑加真,滞立在北京的街头。这位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参与者,将自己整整30年的人生脚印留在了北大荒的转业军人,这个让自己原在首都生活、同为军人的妻子也做了东北移民的丈夫,在荒蛮与肥沃的艰辛中生育了一女一子的父亲,感到了深重的失望。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没有“当年转业官兵来北大荒的部队历史资料”,更遑论其中的一个士兵了。在北大荒的日子里,郑加真见过来农场“接受改造并要发挥作用”的女作家丁玲和大诗人艾青,也同聂绀弩、丁聪在一个碉堡式的小屋里共事过,更见过他们重新恢复工作后写下的著作,艾青这样写道:不知道把自己遗失在哪里,在失物招领处也领不回来。而此刻的郑加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原因,被遗失了。
三十多年前,摘下军衣上的上尉肩章和领花,摘下八一帽徽,同战友们一起,搭乘专列,从春暖花开的首都,来到雪花飘飞、大地封冻的北大荒。在寒风凛冽的密山车站广场上,随同各地来的成千上万战友一起待命分配。这里(指密山县)是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枢纽部,又是调拨人马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在人山人海的喧腾声中,像调拨货物一样,我们一百多名转业军官被分配到松阿察河畔的一个新建点。这个仅有6栋草房的荒原小村里,简直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来的百多名转业军官中有空军、炮兵、坦克兵;有参谋长、营长、主任;有搞作战的、有搞情报的,也有搞领航的、气象的,有翻译、有打字员、有器材员,也有医生……就是缺少从农村来的庄稼人。
我们这伙外行农民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队,军事工程科科长当了队长,作战科长、营参谋长、训练参谋分别当了正副小队长,搞防原子、防化学的参谋当了播种机的农具手,坦克教员成了拖拉机手,翻译进了马号喂马,还有几个参谋、助理员进伙房给我们做饭烧水了。于是,伐木、割草、盖房、修路、翻地、播种……打开地图,在祖国东北角原来空白的地方,我们虔诚地画上了一颗小小的红五星。
当年十万大军在荒野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生产队,何止几十个、几百个,而是上千个!作为机械化国营农场的细胞,它组成了规模颇大的国营农场群体。如此众多的红五星,一下子出现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北至黑龙江,从小兴安岭山麓,到完达山南北,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显示了这支庞大移民队伍的布局。
可是,在北大荒填补了“空白”的十万官兵的业绩,在历史上是块“空白”,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扫兴和心酸的事。
《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主编郑加真发问了:这真的能遗忘吗?
彭德怀批示:先小搞试验
我的采访,从下飞机的下午,一直进行到晚上。郑加真在家中留饭。老爱人生病住院,女儿陪在病床前。我跟郑加真说,都是先后垦荒人,我们以最简单方法喂饱肚子为标准。郑加真便以电饭煲热饭,打电话到居民区旁边的餐饮小店,要了两个菜,一是鱼香肉丝,这是常见的江南家常菜,再一个是“地三鲜”,也就是土豆、辣椒和茄子这东北地界蔬菜“主角”的烩炒组合。一个鸡蛋几片葱花,便是自制的“甩袖汤”。郑加真念念不忘地讲:我一直最喜欢吃的,是上海的油条和豆制品烤麸。
在郑加真“滚瓜烂熟”的叙述里,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史的脉络,十分清晰。
当年二战结束,小鬼子滚蛋,奉党中央命令,我解放军争分夺秒抢先进入东北。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里就明确指出:“除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1946年决不可空过。”以老红军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为代表,在黑龙江建立了100多个小型农场,这就是东北农场最早闪耀的星星之火。
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会议上,陈云、李富春号召北大荒要创建“公营机械农场”。周光亚创建的通北机械农场,就是电影《老兵新传》的故事和人物雏形。第一个省级国营农场管理机构成立,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北大荒农垦系统把2007年作为黑龙江农垦总局成立60周年的根据。
我跟郑加真说,去年夏天,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我来到黑龙江方正采访,那里有一个“中国唯一的、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的日本人公墓”;在查阅资料时候,我看到,在1946年“中共北满分局陈云到方正县视察”。这一点与现在叙述的农垦史的起始由来是完全一致的。
1948年10月,东北全境解放,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迁至沈阳,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作为东北根据地大后方的北满、西满五省,先后接受了在战争中负伤致残数以十万计的荣誉军人。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战争还在继续,生产尚未恢复,财力物资匮乏,荣复军人安置问题矛盾尖锐,这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中央军委成立荣复军人管理委员会,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兼任主任。从1948年到1951年,东北荣复军人管理委员会先后建立学校和工厂,荣军农场也就此诞生。朱德总司令为首届荣军劳动模范大会题词。
毛泽东为“萌芽乡师”题词。乡,是标志农村种地;师,是半耕半读的师范学校;萌芽特指开始。这是当年农垦形象的高度概括。
紧接着,东北军区对解放战争中投诚、起义、被俘的人员,由5000名解放军带领,创建了7个“解放团”农场。
1954年,由苏联政府援建的大型机械化谷物农场友谊农场,在黑龙江择址建立。一支由国务院组织的垦荒大军抵达北大荒。同年,由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协调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从山东北上,开赴北大荒,创建3个农场。1955年,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自组织的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从京、津、冀、鲁、哈纷纷北上,会师北疆。
我说,对于北大荒的农垦开发,国家一直处于高度关注和持续运行之中。郑加真继续说道,尤其要提到的是,王震率领的铁道兵来到北大荒。
1954年6月,铁道兵司令员王震赶到小兴安岭看望部队,省委书记欧阳钦跟王震说:北大荒“荒草齐天,渺无人烟,它相当好几百个南泥湾,够你开发的”。王震笑问:我带兵进你的地盘,欢迎不?欧阳钦笑着回答:我双手欢迎,你去密山县城,就会看到火车站前立着一个三五九旅烈士纪念碑。战士们为解放密山献出了生命,在流过血的土地上屯垦建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经过试点,1955年8月14日,王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圈阅、批示:“刘、朱、周、陈、小平同志阅退彭”。彭德怀批示:“王震同志提议可以先小搞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再扩大一些。”
从1954年到1956年,铁道兵一万多复转官兵,从南方铁路工地开赴北大荒。王震对领头进军北大荒的一位师长说道:你是打头阵的,是去点火的,得搞个样子,以后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从此,中央直属垦区铁道兵农垦局成立,所辖13个农场。
“宜粗不宜细”的垦荒志
政权新建,国家平定,与不同对手之间进行的武装战争逐一获得胜利结束,人民军队部分人员的转型,一切都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理所当然的轨道上。面对荒野,面对严冬和酷暑,所有自然生存条件的艰巨性,以及物质匮乏等等困难,在军人这两个字的前面,统统轰然败退。因为国家需求,也因为对于这份“国家需求粮食”如是重大使命的遵循和理解,也同样因为对于为完成这份使命的急切和陌生,在农业生产摸索中产生过深痛的的失误和教训。
郑加真说道,将近60年的历史,再写几十万字、几百万字,也说不完道不尽;对于编写北大荒农垦史志,十年辛苦,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完整的,力求北大荒农垦史的递进脉络整理清晰,既谈成就,也不回避失误。上级编史修志的基本方针是,“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但在某些方面宜粗不宜细”。
现在定稿的北大荒农垦史,名字叫作《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计有80万字;历时十载,七易其稿,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全面系统地记叙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群的开拓和建设,是目前全国农垦系统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叙北大荒开发的志书”。
在编撰北大荒农垦史志时,郑加真从未如此深入和深广地接触到历史进程细节,使他感觉,在完成“官方”史志的同时,还必须用自己这支作家的笔,记录这份辉煌和艰巨同在,歌声和血泪共存的伟大历史。从1995年开始,郑加真写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继而又写了《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练》、《崛起》),比定稿史志的80万字还要多了30万字。郑加真觉得言犹未尽,继续写成的《中国东北角·拾遗》出版。郑加真作为对北大荒农垦历史“通天晓地”的人物,成为黑龙江另一位作家的笔下主角,记录这位“先军后民南人北国”人生的15万字,书名起得是很低调的,仅仅是“黑土留痕”。
我和郑加真谈到1958年的“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他说——
如果将1957年前的北大荒开垦,基本比喻为循序渐进,1958年的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则是暴风骤雨式的宏大举措。1958年3月,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针指导下,全会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于是,全军总动员。
一切历史都是当时的当代史,很难说,“十万官兵”这件事不带有当年“大跃进”的烙印。当年解放军号称500万人,脱下军服的10万官兵,占到全军现役军人的五十分之一,其中6万多人是各级尉官,这个尉官人数在全国尉官数量中的比例,我至今不知。这些人学有专长,年富力强。国家需要粮食,作为军人,他们就像枪一响上战场一样,立即奔赴疆场。他们中本来有多少人是可以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
30年来,我结识的命运曲折的战友无计其数,从他(她)各自的曲折经历中,逐步了解十万大军开发北大荒这个伟大历史背景下如此错综复杂的个人命运。我尝试着从成就和代价相结合的角度,来观察我的战友、我的荒原、我的军队、我的国家。这是豪迈的,也是残酷的。这是壮丽的,也是惨痛的。如此复杂的群体,如此巨大的转折,如此惊人的奉献和牺牲,如此高代价的移民开垦和高速度的大进军,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言辞和一般史书来表达了。
我说,北大荒农垦史多少年来不能定稿,是因为有些事情始终没有固定的“说法”,所以一直拖着。
郑加真解说,北京军事博物馆当初说没有找到十万官兵的番号,其实当年总局这一级也是空白。年代、事件、人物,还有大量的历史细节,基层的真实情景,农垦史办公室的人坐在办公室里,是得不到什么真实情况的。最了解情况的人,是下边农场的人。总局的人下去,跑得再细,也总是隔着一层。我就要求,每个农场都要搞一本场史,定好要求,定下时间,到时候交卷。所有的农场史都搞好了,交上来汇总,整个北大荒农垦史的大脉络,就都有了。“起码是有了抓手”。
后来,100多个农场的史志都交上来了。
郑加真缓缓打开书橱,一人多高的书橱里,“挤满”了黑龙江农垦总局所辖100多个农场的“分卷场史”。赵光、友谊、宁安、852、8511、洪河、汤原,等等,这些熟悉的场名,现在印刻在一本本场史厚厚的书脊上,闪动着朴素的光芒。
赢得未来,是牢记过去的最佳方式
我向郑加真提了最后一个问题:对于1968年后知识青年的“屯垦戍边”,你的农垦史是怎样表述的?郑加真拿出一本他主编的《北大荒画史(1947-1987)》。里面全是黑白照片,图文并茂。
1968年后,北大荒垦区,也就是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各地知识青年共计45万人。从1968年到1973年,垦区每况愈下,当年国家对兵团基本建设累计投资8亿元,而兵团累计亏损10亿元,平均每年亏损1.6亿元。这六年是垦区历史上经济效益最差时期。
1973年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
在将中国诸多城市青年的就业和生存压力转移到东北农场5年之后,50余万知识青年向国家伸手要饭吃的窘境,依然如旧。
我做过十年兵团农垦战士。当年口号“小镰刀战胜机械化”,言犹在耳。面对一个农场几十万亩丰收的小麦或大豆,愚蠢地放弃机械化收割,动用人力用镰刀在地里跋涉,真是人困马乏,遍地浪费。郑加真摆摆手说,1958年还有过“裤播机”,就是把人裤子的裤腿扎起,里边装满种子,再让裤子“骑”在脖子上,双手抖动裤腿,边走边撒地播种。“如果说因为客观原因,在大型机械无法周旋运行的地头边角,人工做点手工补充,那完全应该。只是,在艰苦奋斗的旗帜下,我们曾经那么僵硬地以为精神万能,牺牲万能,以太小局部的人力补充,作为全局性质的道德号召,这实在是违背科学。北大荒农垦史上有个巨大的教训,就是一批又一批地到来的垦荒者,但总不能避免地有部分的后来者,过于强硬地否定前人历经千回百转、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经验。似乎前人已经付出的学费不是学费,非得自己再付一遍。”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1997年,也就是北大荒垦区50周年纪念日,《黑龙江日报》以“黑土地的跨越”为题,报道了北大荒农垦的新局面:“位居中国农业机械化之先的黑龙江垦区,历经50年机械化、现代化的洗礼,正发生新的可喜的变化。”今天的垦区,正在筹备2007年垦区60周年纪念活动:昔日荒野已耸立起140多座农业城镇,垦区的粮食总产从1995年100亿斤增加到2005年的200亿斤,十年翻了一番,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到2007年的“60周年纪念”,还有两年时间,肯定也会有长足的增产,至于垦区粮食总产要达到300亿斤,也毋需十年。关键就在于以史为鉴,居安思危,重视历史上的经验和失误。
说到北大荒精神,郑加真回答,过去一直有16个字的说法,就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而我在开掘尘封的历史之后感到,对历史上做出贡献、值得关注的部分移民来说,还要加上一条,四个字:忍辱负重。
到达哈尔滨采访的日子,正值郑加真获得黑龙江省“终身成就奖”提名,他在赶写“自己的文字”。在2000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来到北大荒垦区视察,在被接见的18名垦区“三老”代表中,郑加真是唯一的“北大荒文化界人士”。
听着郑加真的讲述,看着挤满100多部农场史志的书橱,我感到一种阶段性质的安慰。然而,胸中涌动着最浓重的感觉,是历史尘埃的永不落定。北大荒农垦史已“宜粗不宜细”地编撰完毕,如是编史的原因:其一,中国需要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农场就是这样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其二,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先行者和后来人,都要记住今天北大荒农场在中国商品粮市场地位的艰辛来历。忘记过去意味背叛,而牢记过去的最佳方式,是把握今天、赢得未来。
79人用1500元钱在北大荒创建通北机械农场
撰稿/郑加真
在上世纪60年代,《老兵新传》是一部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电影中的主人公原型,其实就是原辽北军区司令部作训科长周光亚。这个曾当过抗日义勇军战士、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老兵,他带领战士顶风冒雪,在日本开拓团废墟上创建通北机械农场时,只有79人。
1947年7月,周光亚先到三河地区,对白俄经营的机械耕作的农场,进行了一个多月考察。11月,他带领三名通信员,到通北县赵光站,冒着风雪,实地踏查。当时,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人财物极端缺乏,他拥有的仅仅是几个人和上级拨给的1500元钱。荒原上赖以栖身的唯一的房屋,是日伪开拓团训练学校旧址,侵略军溃败时遭到破坏,只剩下断壁残垣。他们借来门板,割几捆草堵上窗户,在地面铺上厚厚的羊草,就算安家落户了。野外白雪茫茫,寒风呼啸。室内冷气嗖嗖,四处透风,他们风趣地称为“五风楼”。夜间没有人敢脱衣服睡觉,都穿棉衣戴棉帽。周光亚想出了御寒的绝招:用烧烫了的砖块取暖,搂着羊羔睡觉……白天踏查,晚上就在“五风楼”里制定建场规划。
听说轱辘磙河桥下有一台日伪开拓团扔下的火犁,周光亚就带领人马,驾着一辆大车去了。到那里一看,天寒地冻,一台“万国牌”旧机车结结实实地冻在泥潭里,纹丝不动。他和大伙就轮流喝一口烧酒,下到冰冻的泥潭里又刨又挖,总算把这台破旧机车挖了出来。这就是通北农场的第一台拖拉机,以后,又用战场缴获的福特、法尔毛、小松等杂牌机车,组成了第一支拖拉机队,投入了开荒生产。
有一篇关于马架子生活的回忆文章。作者是当年从军校转业来的少尉文化教员,描述了住马架离不开蚊帐以及蚊帐的妙用,风趣横生,堪称一绝:
“北大荒嘛,‘荒’字拆开,上边是草,下边是‘水’,草多水多,蚊子肯定少不了。我被分配在八五三农场四分场,也就是颇有名气的雁窝岛。岛上的蚊子多得邪乎,劈空一抓就是一把。到了晚上,蚊子全体出动,‘嗡嗡’声不绝于耳,都涌进马架子来了。这样,从部队带来的蚊帐就成了我们的传家宝。收工回来,一进马架,就得钻进蚊帐,否则,蚊子就会把你团团包围。蚊帐在白天也必须落下来,四角边用被子压得严严实实,防止蚊子乘虚而入。进入蚊帐时,不忙脱衣服鞋子,先站在帐前用军帽大力忽闪,为的是请紧追不舍的蚊群让路,然后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开蚊帐一角鱼跃而入。进入‘阵地’之后,开始‘构筑工事’,脱下水鞋谨慎地一只一只从蚊帐边伸出扔到地下,接着脱下衣裤,全部压在蚊帐四个底角和底边。蚊帐下面凸出一个方框,为的是不使自己的肉体直接挨到蚊帐,否则就有隔帐被咬的危险。‘工事’筑好,接着是‘扫清残敌’,哪怕刚只是掀动蚊帐一角、急速窜入的一刹那,随之而入的‘蚊敌’已不计其数。这时。一盏盏探照灯(手电筒)开始在各自的帐中搜索,一声声高射炮声(拍巴掌)此起彼落、连连射击。每日一次的‘地对空’激战就此开展,而且经常开展‘歼灭敌机’大竞赛。各个帐内纷纷报数:一架,两架……三架、五架……十架,二十架!最后各报总数评出对空射击能手。我曾以一次歼灭‘敌机’59架而荣获亚军,其中不少蚊子身上已见血了……马架里的蚊帐成了垦荒战士的小乐园,它既是卧室、办公室、学习室,又是文艺晚会的舞台。被垛拉过来就是炕桌,手电筒拧下玻璃罩一立就是烛台。看书的,写信的,甚至邀请一位战友进帐来下棋,大战‘三百回合’,以及海阔天空地聊天,你一段我一段地拉起文艺节目来——‘蚊帐晚会’便应运而生!”-
链接:
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政策,始终与国力的强盛与衰败联系在一起。1949年3月,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各兵团战斗任务以及胜利后接管地区的问题,并做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王震率领的一兵团二、六两军向西北进军熛群笥得了扶眉、陇东、兰州、秦岭、宁夏、河西战役的胜利,基本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个省,挺进新疆东大门。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10万官兵宣布起义,新疆得以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剿匪、建党、建政成为部队的主要工作,同时,一条更重要的战线在天山南北拉开了序幕,这就是大生产,屯垦戍边,为中国西部开业奠基。
2003年5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发表了《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在第九部分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发展和作用,白皮书写道:
“1954年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在自己所辖的垦区内,依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在中国西部,兵团的特殊组织形式,是中央支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各民族相互支援的有效形式。兵团的百万儿女,始终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新民周刊 侯友权)
北大荒半世纪艰苦创业 5万多人长眠黑土地
撰稿/郑加真
在我案头摆着一份1958年转业军人的统计资料:从1947年开始,陆续进入北大荒的转业复员军入,共8批次,累计14万人。截至1985年末,仍留在北大荒的转业军人共7万多人。其中老红军40人,抗日时期参军的2000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16000人。残废军人1500人。年过半百、花甲的已达20000人。因公牺牲、长眠地下的3000人。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自
然病故、在各种事故中死亡……
据1995年资料表明:北大荒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艰苦创业中,已有5万多人的白骨埋在这块黑土地上。遗憾的是未查明转业军人数字。但是,可以肯定:在这5万多长眠者中间,转业军人占着很大的比例。因为他们大都年近花甲,有的则是“古稀”、“耄耋”之年。
当然,其中也不乏英年早逝的科技人员、城市知青和从祖国各地来的垦荒者。如果说今日北大荒面貌巨变、万象更新,那么,这一切与长眠者紧密相连。
没有5万多长眠者的昨天,就没有北大荒的今天。在这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年每平方公里还摊不上一个拓荒者;如今,每平方公里已埋下了一个拓荒者的忠骨了。
无论走到哪里,农场或是工厂,城镇或是生产队居民点,你在聆听人们讲述开发史、参观他们的当今建设成果之后,准会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公墓,或者坟包……有的立碑纪念,有的仅仅用木牌标志死者姓名。这些安静的公墓和坟包,俨然是北大荒的庄严、肃穆的“八宝山”公墓了。他们讲述的历史都要从这里开始,而今日矗立在荒原上的一切:林带,公路,麦海,电视塔,农用飞机场,粮食处理中心……都与长眠者有关,凝聚着他们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
人们都这样对来访者说:“这是咱们单位的八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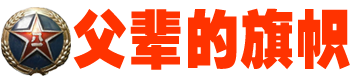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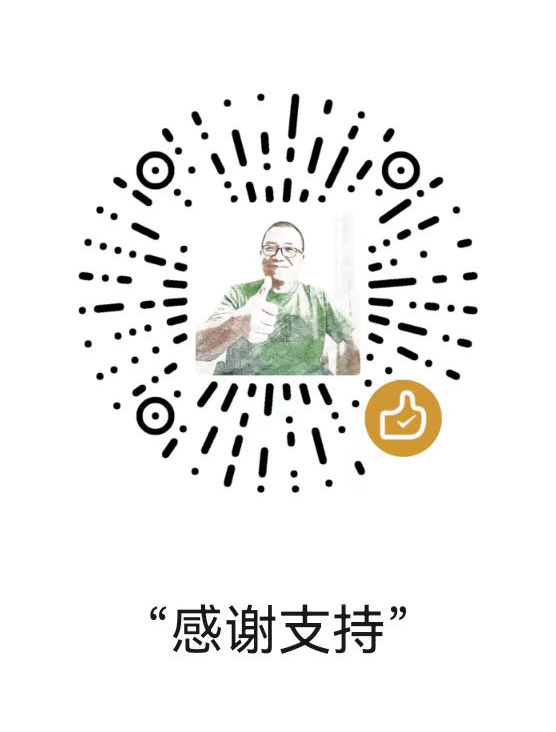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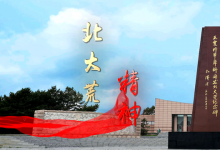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