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北大荒,只有北大仓,夏季麦浪翻滚,冬季冰雪晶莹,一切如梦似幻。我79年出生在黑龙江畔的逊克农场,6岁读书时离开。逊克农场在我的记忆中有如童话,水清草绿,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连队养的小白马,可以自由的在街上跑来跑去,河边的小乌龟,似乎有着金色的外壳,自家的菜园中有“贼不偷”的绿柿子,有可以当水果吃的彩色甜椒。因得父母的照顾,以及当时所有人同一化的生活水平,倒是未觉生活的苦。
童年渐远,人生渐长,重回北大荒的心愿也越来越迫切。近日偶得陈绪章、陈芳路所著的《北大荒的记忆》,这似乎向我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记忆中的世界。原来,北大荒也有着前世今生。
这本书是由陈芳路根据其父陈绪章先生在世时写下的日记、笔记、诗歌,以及一些资料图片编辑、整理而成,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陈绪章令人感叹、唏嘘、敬佩的一生。该书看似记录的仅是一个人的“小历史”,但实际上陈绪章个人的命运也代表着十万拓荒官兵的命运,他思想的轨迹也是那一代人思想的轨迹。在陈绪章个人“小历史”背后,透射的是整个北大荒的拓荒史,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

陈芳路的父亲陈绪章1929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参军前书读到了省立高级职业学校,参军接受专业训练后,在航空学校任学员、教员。陈绪章文能写,武能干,勤劳朴实,一颗忠心向着党。他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即使在申请入党的过程中,因一个亲戚的家庭出身问题受到了影响,在历次运动中,总是被作为重点检查或审查的对象,他也丝毫无怨,还不停地反醒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个人的命运总会与时代裹挟在一起。陈绪章在部队想入党不得,但党中央十万官兵转业集结北大荒的号召,令他看到了转机。他认为自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仅仅一个晚上,他就做出了一个可能影响他及子孙几代人的决定,写出了热血沸腾的向北大荒进发的申请书,在想象中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北大荒农场的垦荒建设并非一日之功,也非三五年可以达到现代化。当年的北大荒,人烟稀少,这里没有为人准备的基础设施,只有冬天里零下四十度,滴水成冰的温度,还有那怒吼的北风。以陈绪章为代表的复转官兵们,以为到了北大荒,等待他们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丰盛的,但事实上只有萝卜汤、大碴子,而且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复一日。在这里,没有时间给他们适应环境,没有时间让他们调整南北生活差异,来到的第一刻,场长就吹起了“冲锋号角”:修渠开荒、抢种、盖房子,盖房子的材料要自己找、自己造,砍树、编条子,盘土炕,所有的活都要自己干。要想在这里扎下根,活下来,只能适应适应再适应,大自然给你什么条件就要利用好什么条件,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的命斗。
陈绪章在当时,无疑是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战天斗地运动中的胜利者,一年后,他如愿入了党,他也在文章中说这是他一生中的巅峰时刻。心中的目标达成,想必他当时的幸福也是溢于言表吧。在当年,人的幸福就是那么简单,可以是上级的一句肯定,可以是一个热窝窝头,也可以是一个遥远的希望。那是多么真纯、简单的年代。

其实,陈绪章在当年,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农场,但他将个人的境遇看得太轻,将农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比如,在1958年冬,上面要调一批从航校来的人去沈阳飞机制造厂,陈绪章无疑是符合条件的,但就因生产队长的一句“希望你能为了厂里的工作留下来”,陈绪章便放弃了去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机会。人生命运难料,当时选择离开,未来未必会一帆风顺,但选择留下,艰苦、劳累,就一定如影随形。如果,那年陈绪章没有放弃到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机会,也许他及他的儿孙们的命运都将被改写。只是,人生没有如果,青春远逝,时光不会重来。
看着书中陈绪章在晚年,瘦小而单薄的身影,令人心痛不已,他在年青时透支了太多的体力和精力,常年的高负荷劳动,令他染上了一身疾病,终于由一个精壮的汉子变成了一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小老头。
陈绪章后来在当地的学校执教,虽自身经历了几番沉浮,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学校、学生,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始终都在尽心竭力。在教学上他是攻坚手,在劳动上他身先士卒。他拿得起放得下,当一名普通教师,就是踏踏实实搞教学;当上校长更是以身作则,教育、劳动、管理一手抓;再次下放到加工厂劳动,就带着劳动改造的心情,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回归教育岗位,则以感恩的心报答党的信任。“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句用来形容陈绪章,形容那一代痴心不改的复转官兵再合适不过。
读这本《北大荒记忆》,令我仿佛看到了我出生之前,那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没有陈绪章那一代复转官兵的拓荒,没有他们用青春浇灌出的肥沃土地,我父母这一代知青到了那里也许要吃更多的苦头,而我,也将不会拥有那些美好的童年记忆。老一代拓荒转业官兵、以及一代垦荒知青,他们用青春热血、半生执着、一世辛劳,甚至是几代人的留守,哺育了那片土地,让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一片如童话一般梦幻美丽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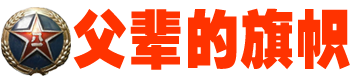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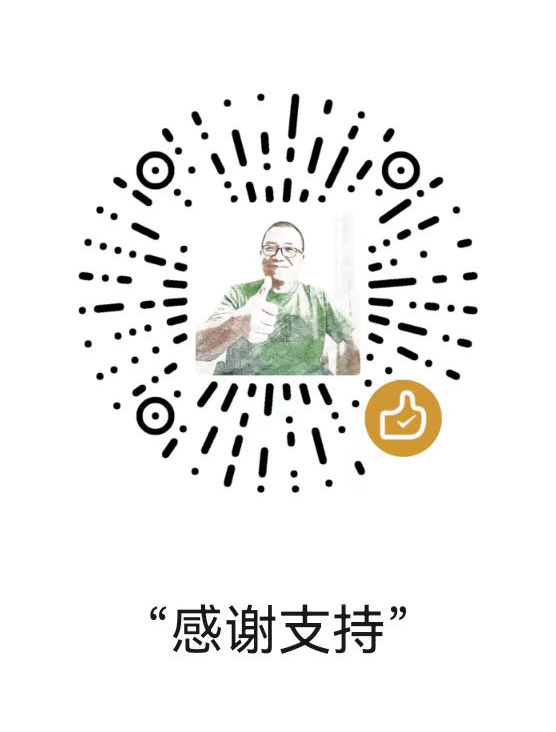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