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北大荒孩子一样,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偏僻的小连队里。我们的父辈大多是五十年代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听从王震将军的指挥来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官兵和支边青年。
资料图
我的家乡在八五二农场一个偏僻的小连队,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曾经,我们的住区都是一排排红砖红瓦的房子,四家一栋。由于家家没有院落,通透开朗得就像部队的营房一样,整齐地掩映在一棵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五湖四海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各种风俗、语言、饮食、习惯等相互交融、彼此渗透,形成了北大荒特有的、极具个性的“黑土文化”。这里地广人稀,民风淳朴,那时,大人们白天上班从来不用锁门,东西放在户外也从不会丢失。正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连队的四周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南面不远还有连绵起伏的大山,据说这里属于完达山北面的余脉,所以,八五二地区也称“完北”。每到春天,幽深的山谷里就会传出布谷鸟清脆而有节奏的叫声,山歌一般婉转悠扬。不久,山绿了,草青了,云白了,杜鹃花、山杏花以及五颜六色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也都争先恐后地次第开放了。这时,花香里,鸟语中,机务排的大爷、叔叔们就会驾驶着“东方红”拖拉机在田野里耙地、播种了。远远望去,蓝天白云下,一台台机车就像一只只红色的甲壳虫在黑色油布上蠕动,童话一般……
南山脚下有个“暖泉”,无论冬夏,水总是那么盈盈而空灵的一汪,清澈甘甜,泪儿似地潺潺地在青草的抚慰下,含情脉脉地向东北方向淌去……
那里曾是连队的人最宝贵的补充水源的地方。无论是春天的大田播种、夏天的豆地割大草、麦收,还是秋天割豆子、掰玉米,亦或是冬天上山拉柴禾,只要随身携带的玻璃瓶、半旧的军用水壶里的水喝光的时候,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寻到那里,先掬起一捧甘甜的泉水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再将“家什”灌满,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旁边的那棵一人多高的小榆树迄今为止仍是“暖泉”永恒的“坐标”。
“暖泉”往北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孩子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西河”。从春天到秋天,蜿蜒的河床里,河水自南向北哗哗地流着,汇入连队后面的“黑鱼泡”,直到白雪为它们划上“休止符”才会停止歌唱。
提起“黑鱼泡”,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呢。
听当地的老人讲,很久很久以前,“黑鱼泡”比现在要大得多,水有三丈多深。相传,这里生活着一条“黑鱼精”,有人还亲眼看见过“黑鱼精”游水,仅露出水面的黑色脊背的一斑就有一丈来长,“黑鱼泡”也由此而得名。据说“黑鱼精”很有灵性。有一年大旱,连月无雨,庄稼眼看着就要干死了。万般无奈之下,当地的老乡们就拿着盆碗、摆着供品、敲着锣跪在“黑鱼泡”岸边,虔诚地乞求上天发发慈悲,降下甘露。正在人们祭拜的时候,忽见“黑鱼泡”里腾起一道数丈高的巨大水柱,这水柱直冲云霄,经久不落。人们正惊恐诧异,不一会儿,天真的就下起雨来,旱情随即解除。老乡们高兴极了,都说是“黑鱼精”显灵了,是它上天通报,为民请命,老天爷才降下雨来的。
虽是传说,但“黑鱼显灵”的故事却给“黑鱼泡”平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令人心驰神往、浮想联翩…….
“黑鱼泡”南面有一片糖棋树林,那是我们的父辈在这里安家时亲手所栽,我记事的时候,这里的树木已经是郁郁葱葱了。老师带我们在这里玩过“找宝”,玩过“打仗”,搞过“军事演习”。树上那一串串小刀似的树种,常常变成我们的“零食”,我们的玩具……
“黑鱼泡”北面,是我们连队的试验田,夏天的时候,为了不让成群的麻雀啄食麦穗,大人们在地里支起一个个“穿衣衫”、“戴帽子”的稻草人,我们这些小学生则两人一组,到那里看护,举着棍,敲着锣,奔跑着驱赶着成群的麻雀……
每到麦收的时候,全连的人都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麦收战役中,“抢场”那更是家常便饭。乌云滚滚中,急促的钟声一响,全连男女老少就会像救火似的带上各种家什拼命往场院跑,仿佛自家粮食就要被大水冲跑了一样。那场面煞是壮观,也着实感人!
这时,康拜因、拖拉机也会整日整夜地都在地里收麦子、翻地,忙个不停。“尤特滋”(一种胶轮拖拉机)则本着“多拉快跑”的原则,穿梭于麦田与连队之间,忙着往场院拉麦子。而我们这些正值暑假的小学生们也会被安排到场院翻麦子,或到地里跟在康拜因后面拣麦穗。两人一组,一组一段,拣完这一段便可以坐在麦秸堆上编蝈蝈笼,编好了便可以捉来蚂蚱或蝈蝈放在里面,然后再塞进几片青草叶或面瓜花当它们的食物。休息时,我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连队食堂送来的盼望已久的“加班饭”,一边在弥漫着麦香和新翻的泥土气息的空气里感受着美好生活带给我们的惬意和满足。醉心于“白吃白干”的孩子们在兰花多情的摇曳中聆听着蝈蝈们悦耳的吟唱,欣赏着蚂蚱们欢快的劲舞,尽情地享受着,怡然自乐……
渴了的时候,我们便会跑到南山脚下作业站的那个茅草屋里去喝水。那里住着一位高高瘦瘦、后背微驼、满脸胡须的养蜂老人,他总是在炎热的夏天为我们这些参加麦收的孩子准备两大桶蜂蜜水,那冰洌、甘甜的蜜汁浸润着我们焦渴的肺腑,滋养着我们稚嫩的心田,一直甜到今天……
太阳落山了,我们就会坐着“尤特滋”回家。一路上,我们躺在装满麦子的车斗上,嗅着身下麦粒的清香,在车斗的颠簸中仰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感受着凉风拂面的惬意。每每那时,一天的疲劳都会荡然无存,而那种沁入心脾的悠然和畅快,则渲染着我的少年时光,犹如出笼鸟儿一般……
是啊,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长大了,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大都是城市来的知青,他们的普通话都讲得很好。我们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说话的口音可谓是“南腔北调”,而我们这些学生却个个都是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当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些教过我们的老师们。
在教过我的老师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位北京知青,她叫王卫。王老师修长的身材,单眼皮儿,瓜子脸,长得十分秀气。她总是穿着一件绿军装上衣,一条米色的凡尔丁裤子,两条又细又长的辫子总是垂在身后,走起路来左右摆动,仿佛两条黑色的柳枝,飘逸中透着俊俏……
王老师性格特别温柔,在我印象中,似乎从没看见她发过火,更没有暴跳如雷地训斥过我们。每次王老师从北京探亲回来,都会带给我们每人一件小礼物。我第一次收到的是一支自动铅笔,那时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动笔,那些笔五颜六色的,发给我的那支是苹果绿色的,那一抹鲜艳的新绿一直印在我的心底,让我至今想起来还为之陶醉。自动铅放在老师抽屉里,谁用完了谁去管老师要,总觉得那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
王老师返城的时候,我已上了初中。那天晚上,我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去向老师告别,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想到此一别,也许再也无由相见,心仿佛有种一下子被掏空的感觉。
同学散去之后,王老师要到相临的八连去,那里有个老师的同乡,第二天他们要结伴而行。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走,我们默默地陪着王老师,想多送她一程。那天晚上月光皎洁,月光下,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止不住地滚落下来。一种平生从没有过的孤独、失落和悲伤第一次潜住了我少女的心……
走到两个连队的中间,王老师劝我们别送了,可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心里真的很难过,不知说什么好。老师搂着我俩的肩膀,不停地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去北京找她,还告诉了我们她家的住址,我只记得是民族文化宫附近。那时候傻傻的我不知道北京有多大,以为到那里找人也像在连队,一说找谁,哪怕小孩都能把你送到家门口。后来,我去过北京,我知道这里有我日夜思念的老师,可是,茫茫人海,要找到我的老师岂不是像大海捞针一样难吗?
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师依然是清清瘦瘦的样子。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忘记她,同学聚会的时候,王老师是我们永恒而亲切的话题,是我们所有同学的思念。我们曾设法打听她的下落,得知她返城后到了北京无线电十厂,打电话过去,那边的人说,她早已退休,他也不知道她的地址和电话。这几年也偶有知青回访,我们盼着王老师也能有一天回到这里,看看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们这些她教过的学生很想她……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王老师教了我们好几年,我们却没有一张与王老师的合影,也没有一张王老师的照片,而王老师却是我们每个同学脑海里长长的思念……
苦短的人生旅途,三十多年的分离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但那个年轻、秀气的王老师以及那段温馨的时光却早已绵延成我们每个同学脑海里长长的思念。她烂漫了我们的童年,渲染了我们的青春,也茁壮了我们原本瘦小、羸弱的生命……
如今,这里已经由生产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当年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如今也已到了不惑之年,我们之中有的务农,有的做工,有的当了干部,有的随父母回到了南方,也有的随夫去了外地。而我从师范毕业以后,重又回到了高中时的母校,做了一名教师。我知道,离开脚下这片黑土,我就如同失去了根基,感觉心在飘摇、寝食难安……
哦,故乡,你是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哦,童年,你是我记忆中永恒的乐园!
哦,思念,你是我生命里最美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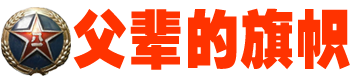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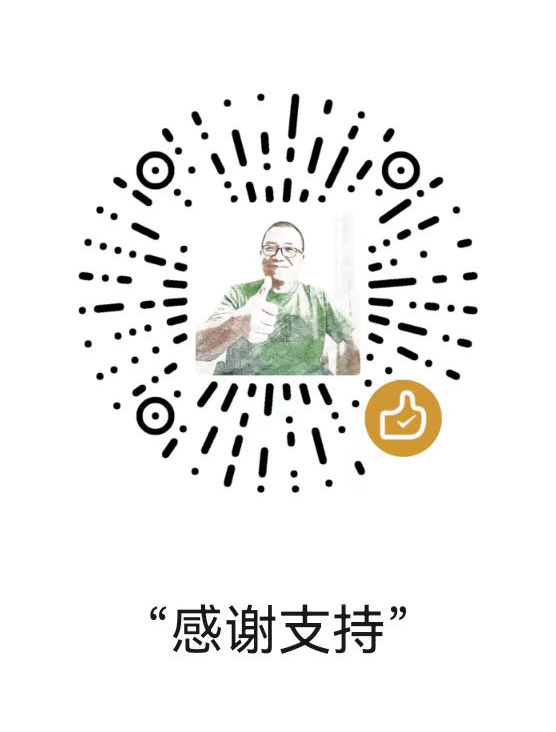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