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五三农场二十一连宁波、上海知青“北大荒回访团”回来已经一年有余了,回来后我陆续写了几篇回访人物系列,然意犹未尽。隔了一段这么长时间,再来续写其他几位回访人物,就写作效果来说,似乎有些影响,因为当时有些情景回忆起来比较困难,不够清晰。写作的冲动和激情更会随时间流逝而减退。但北大荒确实是个神奇的地方,北大荒的友情它会穿越时间隧道。当你真正静下心来,凝神沉思的时候,那种思念和激情又会重新萌动。正像潮起潮落一样,它会退落,但永远不会消失。思念的潮水,又会扑面而来。
今天,我的目光落在了指导员孙荣的身上。在我的眼中,他永远是我的指导员,虽然他后来职务多次升迁,但我一直叫他指导员,从未改变,也从不带姓。这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也是我一直想动笔细细描述的老军人、老英雄。在他的身上,我们会发现许多闪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当今的社会已渐行渐远。
1969年5月31日,我们十八位宁波知青到了北大荒,即被分配到八五三场部工程三连(二十一连前身),当时的李国忠连长和孙荣指导员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第一眼看到孙荣,他的军人风度就深深吸引了我。他当时穿着一套洗得十分干净、几乎发白的旧军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几乎只穿军装,很少见他穿其他服装),笔挺的身板,平坦而宽厚的肩膀,一起一落几乎标准正步走的铿锵步法,无不透着真正军人的不凡气概。令人惊奇的是,时间并没有冲走他的军人风貌。去年8月15日,在红兴隆管局隆盛大酒店,当我们回访团一行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腰板依然硬朗,军人的味道依然浓烈,其时他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
与指导员孙荣(前排左三)合影留念,后排右一为孙荣大儿子玉森。
指导员是河北滦县人,1946年入伍,41军的,该军是四野王牌军之一(李连长27军,赵副连长38军的,我连的干部均来自战功显赫的英雄部队)。和李连长、赵副连长不同的是,指导员不仅去了朝鲜战场,而且亲身参加过波澜壮阔、腥风血雨的解放战争。我当文书后,多次听他讲述过他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解放战争场面。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冲在战斗第一线的军人。他亲眼目睹多少个战友在身边倒下再没有起来,他亲身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辽沈战役中的打锦州、打四平,都是极其惨烈的战斗,他都参加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他也亲身参加了,“塔山阻击战”已成为41军最辉煌的战功和解放战争经典战例被载入史册。在平津战役中,他参加了攻打天津的战役,由于傅作义的大部队在北平是和平改编的,所以平津战役中真正的硬仗是打天津。我曾经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纪事》一书中(此书为天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编写,范围很广,其中也包括我们二十一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在打天津时,孙荣曾带着枪,跟随部队首长面对面与陈长捷谈判(陈为国民党天津守军总司令、中将),该书第一页图片中的第一张照片,即为我连天津知青张伯韦探望孙荣指导员时的合影,并作了说明介绍。我估计此情节大概为指导员向张伯韦披露的。那个陈长捷后来被我军俘虏,成了战犯。傅作义在陈长捷事情上一直心怀内疚,正是他命令陈长捷死守天津的,最后北京和平解放,傅自己也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宾(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由于傅作义的说情,陈长捷成了1959年最早释放的十名战犯之一,并到上海文史馆工作。“文革’中,陈长捷不可避免地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他生性刚烈,不甘受辱,亲自用菜刀劈死妻子,然后自杀身亡,极其悲惨。此为后话,顺便提及。
指导员英勇善战,战功赫赫,在部队时多次立功受奖,我看到过他不少戴着奖章年轻时的照片,真是英武。指导员参加完解放战争又随41军入朝赴战,后又转战北大荒,可谓戎马一生,铮铮铁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应该提及的是41军至今仍保持着集团军的番号,置身我军现有十八个集团军之列(现驻地广西柳州),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就出自41军。在塔山阻击战中,张万年是41军某团通信股长,他的年龄和入伍时间应该和孙指导员差不多,也是一副威严的军人气概,张万年和我们孙指导员称得上是战友。
隆盛大酒店最豪华的包厢内,指导员早早为我们摆上了25人座的特大酒席,热情的和我们一一握手、拍照。他的大儿玉森、二儿玉林及爱人和女儿玉兰闻讯也从各处赶来赴席,住在管局的李连长二女儿春玲夫妇也参加了。赴宴的还有双鸭山知青孙士杰、马冰茹夫妇,他俩是我连部班战友,孙为粮食化验员,马为出讷员,和我非常熟悉。
在酒宴上致词的时候,我动情地说:“如果北大荒每个连队就是一所军校的话,那我们西大洼二十一连就是北大荒上的黄埔军校,李连长和孙指导员就是我们军校首任校长和政委。”我并提到了指导员最爱唱的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浪淘沙 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換了人间。”指导员的音色浑厚有力,极富磁性。我的好记性把指导员说笑了:“小方,你还记着啊。”回访团的李信龙也直夸我的好记性,说他们早不记得了。然而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不算特别好,特别是现在,只是我比较用心、比较关注细节罢了。没有细节就没有具体的人,从细节可见一个人的真性情。
1970年春我们进军西大洼的时候,我是基建二排四班一名瓦工,排长叫白国安,班长是王保糸(保糸后来成为连队第二任指导员),我那时文弱学生一个,不引人注意。我清楚记得,我引起指导员注意缘起一次早会提问。那个年代“突出政治”空气很浓,早会学习盛行,有一次指导员在早会上点名发问:“什么是‘四个第一’?”连点了好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或不完整。后来指导员就点到我了:“小方,你来试试。”我就起立回答上了:“四个第一”是林副主席(即林彪)提出来的,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我还说了一下“四个第一”互相关系,次序不能随意颠倒的。指导员非常满意,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按照现在的政治观点和理论标准,这“四个第一”肯定是被否定的。但当时却非常红火,毛泽东称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我们抛开政治因素不说,单就语言艺术来讲,我对林彪还是佩服的。文字也好,语言也好,精辟、独到,并充满激情和鼓动力。林彪喜欢用排比句:如天才地、创造牲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等,“四个第一”也是一种排比句型。林彪还喜欢用“最”字修饰,如最大,最好等,且喜欢重叠使用,如最大、最大、最大,我看过林豆豆写的《爸爸叫我写文章》,林彪在文字、语言的运用上确有他的见地和风格。
我当上文书后,大概是1971年冬季,天气非常寒冷。一天我随指导员、连长、赵副连长,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西大洼前往水泥厂,可能是为了落实基建材料的供应。因为那时二十一连建点不久,基建压力很重,且水泥厂基本上是工程营班子,他们三位很熟。那天飘着小雪,路面湿滑,极冷,我把棉帽子都放下来了,捂得严严实实。从二分场到水泥厂的那段公路上弯道下坡处,一辆解放牌大货车超越我呼啸而下,我以为只有这一辆车,就骑着自行车拐到路中央去了,其实后面紧跟着呼啸直下的第二辆解放牌大货车。只听到后面传来指导员、连长:“完了!完了!”尖叫声极其凄厉。惊魂一幕发生了,映入我眼帘的是一辆还冒着热气、四轮朝天的大货车,已侧翻躺倒在公路边巨大的排水壕沟里,驾驶员正从砸坏的驾驶室里往外爬。他是为了紧急避让我,猛打方向自杀式冲入壕沟的。我当时呆若木鸡,连一句“谢谢”都没说。当时骑车,我和连长等人拉开了一段距离(年青人逞能),所以他们在后面看得真切,以为我这下肯定完了。等指导员、连长赶到时,驾驶员已完全爬出驾驶室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伤着没有,指导员答应他用拖拉机把汽车从壕沟里拖上来。冬季北大荒的路面全是冰雪碾成的车辙道,很多车辆都用上了防滑链,行路非常险恶。这种舍身救人,宁愿伤着自己,也要保护路人的可贵精神,在北大荒经常发生,司空见惯。拿到今天,我想这位可敬的驾驶员,应该进入“中国好司机”行列。后来,指导员从十八连调来拖拉机把汽车拉了出来。
当时西大洼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二十一连的许多干部和老职工原先都安家在总场,也在总场住惯了,总场条件肯定比连队好许多。当西大洼上造好最初的几幢家属宿舍后,指导员就第一个从一营林业连搬家到西大洼上,用最简单的行动来表明他扎根西大洼与全连战士同甘共苦的决心。他的这个举动感动了大伙,也坚定了全连职工扎根荒原的信心。后来不少老职工也逐渐从总场搬过来,在西大洼上安家落户。
身为指导员,每逢农忙季节,他总是身先士卒,埋头苦干,把自己当好劳力使用,在田头、在晒场你总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会扔掉一些事务,沉下身来,一干就是一天或连续几天,和职工一起上工一起收工。指导员有腰伤旧病,记得当年割大豆的时候,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在医务室打了封闭止痛针,捂着腰再干,绝不会装装样子,作作摆设,虚晃一枪,然后以各种领导事务为借口打道回府。他的这种踏实劲和死心眼,赢得了职工内心的佩服,包括一些反对他的人(工程三连是场部“文革”派性较严重的单位)。
指导员不苟言笑,一身正气,原则性极强,不会“豁边”,你无法找到其漏洞。我曾经跟一些知青朋友打趣道:指导员他是完全按毛主席语录办事的人,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非常注意细节和小节,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嘴不馋,手不伸,有时甚至于到了苛刻自己、不近人情之地步。这样的人,似乎应该在教科书上才能出现,但他却在我的身边活生生的出现了。在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再也没有碰见过像他这样的干部。大概这就叫用特殊材料铸成的人。从指导员身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当时那么弱小,几乎是游兵散勇般,竟会逐渐发展壮大横扫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并夺取全国政权。这样的干部,现在已凤毛麟角,很难找到了。所以指导员的经历,他的人格的魅力及光芒在当今越发显得珍贵。
和指导员不同的是,李连长则是完全另一种类型,李连长极具魄力和魅力,放得下,拿得起,机动灵活,不苛刻自己,处处散发着天性,可谓性情中人。说来也怪,他俩性格差异如此之大,且都是有能力非常强势的人,却合作得张驰有度、天衣无缝,堪称一绝。我在他们身边跟了那么几年,从未见他俩互不服气或有呕气拆台之举,包容互补,相得益彰,显现出他俩过人的涵养。记得有一次领导班子要开会,已是晚上七点多了,指导员到处找连长,不见影踪,指导员问我:“连长呢?”他挺焦急,因为约定开会时间早已过了,他又是一个守时的人。我答应去找连长,后来在西边一排家属房(张学会家),我找到了连长,赵副连长也在,还有何福兴(上海知青,时任副排长)。原来他们在玩打麻将,且玩兴正浓,忘了时间。经我一说,连长才赶紧去参加会议。上世纪70年代初,麻将绝对是稀罕物,一般人见都没见过,当时的政治氛围,玩麻将不是个好名声,我也不知道连长、老赵他们从那儿搞来这玩意,现在想想也是个谜。从中亦可看出连长指导员截然不同的个性,指导员绝对不会去玩这个。
返城后我也学会了麻将,一段时间内也是个超级麻迷,达到爱不释手程度,近几年才慢慢冷却不少。在我看来,麻将是中国真正的国粹,在海外,包括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京剧等,在近代尤其民国时期,麻将成为官僚、太太、文人墨客之最爱。好像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只有麻将才能忘记读书。可见麻将之魅力。作为娱乐,作为竞技项目,麻将充满变数和哲理,玩麻将如同做人,每个人都有需要的牌拿在别人手里,每个人手里也都有别人需要的牌。
和李连长一样,指导员也是个“抗上”的人,他讨厌溜须拍马,看不起唯唯诺诺,两个人在这方面简直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很长的时间段里,二十一连和分场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常微妙和尴尬状态。受他俩影响,我们这些连部工作人员总觉得和分场不太贴心,我们到分场各业务部门办事,表面上客客气气,但不会深入交流,更不会互交朋友。我又是个极清高的人,到营部看见营长、教导员时,能回避则回避,回避不了打个招呼就完事,不会去讨近乎。现在细想起来,我在二分场十年,职务一直原地踏步(会计兼文书)也没让我上学离开或调离连队,跟上述这些背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分场有些主要领导的潜意识里,我是李国忠、孙荣的嫡系部队和心腹,因而另眼相看。但实际上,我是个没有大志的人,我挺会满足现状,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有失必有得,上帝为你关上了这道门,他也一定为你开好了一扇窗。
宴会上气氛越来越浓烈。指导员深情地回忆起2002年夏天到北京、天津、上海、宁波与各地知青相聚的动人故事,他没有想到知青们对他们这些老领导如此情深谊长,令他感动。所以他这次一定要在管局好好招待我们知青,以尽地主之谊。谈到他和知青间的友情,我不能不提到他和宁波知青戈培莉夫妇(戈的爱人刘列义,上海人,戈的复旦大学外语系同学)间特别的友谊。指导员是一个严谨的人,他和老职工,知青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关系,极少涉及个人来往,但戈培莉却是例外。戈培莉是二十一连西大洼上的首任小卖部代销员,在这个并不显眼的岗位上,她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很早就入了党,并于1972年4月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外贸局工作,事业有成。但她一直忘不了北大荒艰苦岁月对她的磨砺,更忘不了老干部、老职工对她的关心和培养。在连队的时候,她和机务排小车司机赵志宏夫妇关系非常不错。她和朱美华(上海知青)是一对好姐妹,经常上赵家玩,而赵家和指导员家是邻居,久而久之,她俩也经常上指导员家玩了。指导员的妻子是个和善瘦弱的女人,我们都叫她“老病号”,她不上班,是纯粹的家庭妇女。戈培莉、朱美华和“老病号”很讲得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上海工作以后,戈培莉夫妇和赵、孙二家一直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总要送上问候,并时不时寄上节日礼物。2002年,指导员到上海,戈培莉夫妇盛情接待,宾馆住宿费、回程机票等,戈培莉夫妇全包了,可谓重情重义。我们在管局期间,戈培莉夫妇俩还特意到指导员的“新”家去看望,指导员现在独身一人居住在红兴隆老干部敬老院。
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拉着指导员悄悄地问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放在心里的一个问题:“我那时跟了你五六年,你从未批评过我,连一句重话也没有,为什么啊?”因为这和李国忠连长不同,我和连长同住一个宿舍四年多,建立了特别的友情,融合了很多个人感情和来往,如兄长一般。而指导员更多的是工作上的往来,他又是个极严谨极严格的人。今年初,我看到过黄亚明写的一篇长文《记忆1969》,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探亲假风波,受到孙荣指导员严厉批评,并在大会上书面检查。其实指导员也蛮喜欢欣赏他的,从中可见指导员的严格。我是个书生意气的人,自尊心极强,人家以礼待我,尊重我,欣赏我,我会一辈子记着他的好。指导员听了我的问话,笑了:“你做得这样好,我批评你什么啊”指导员这席话使我感动。我一直认为,能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就是你人生很大的成就。在你接触过的一些人里面,在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心中,他们认为你好,他们记挂着你,没忘了你的好,就是你的幸福。他们很看重你,你对他们很重要,这就是你的人生价值体现。
指导员的大儿子玉森(曾任八五三公用事业局副局长)提议我回去后写一下李连长和他的父亲,我答应了。前些日子李连长的故事终于写好完成了,现在我也终于兑现了对玉森的承诺。
在北大荒回访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时不时听到一些老朋友诉说,指导员近些年牢骚滿腹,意见多多。这使人不免诧异,细问之下,才知他对现时的有些干部看不上眼,对他们做的一些事无法忍受。在这位教科书式老英雄面前,我们当今的有些干部确实应该汗颜。
夜幕下的红兴隆,悠闲,宁静,这里已成为昔日北大荒一座正在崛起的新城,指导员和他的儿女们一一和我们握手话别,互致珍重。望着指导员缓缓离去但依然挺拔的背影,令人感慨,也令人起敬。岁月也许会催人老,但有些人的精神却永远不会倒。指导员是我们身边活生生共和国英雄的真实版,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是一个令人充实的特有的时光。我怀念这段时光。他是一生的军人,也是一生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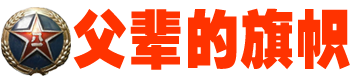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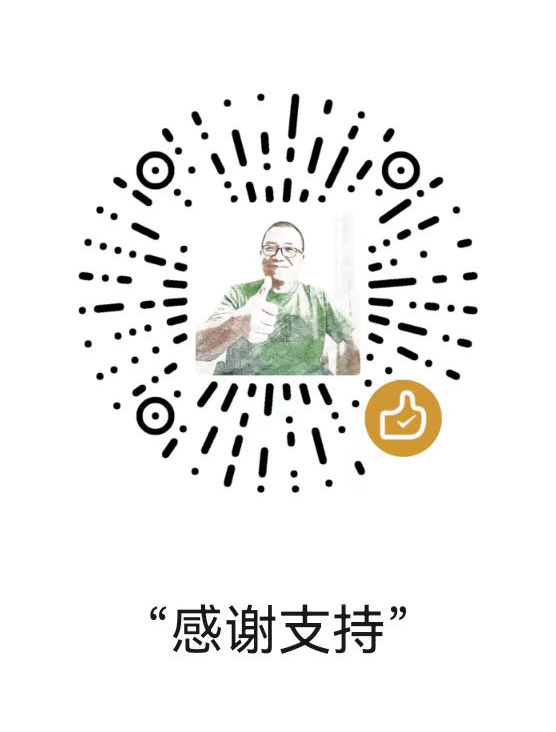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