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连载拾遗(一)
北大荒八五二农场曾有一支特殊改造的队伍
写在前面的话
八五二农场建场初期,随着铁道兵先头部队成建制进入荒原不久,和其它初建的军垦农场清一色军人不同外,还有一支特殊改造的队伍进入荒原,他们身边是荷枪实弹,看守他们的,是江苏来的公安军干部和战士…。
昨天在李强民的博客里,看到了郭小林新作《路,生来就是承受苦难的》《大荒悲悯》之一散文;
郭小林我只闻其名。他是我国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1964年来北大荒八五二农场的北京青青,在八五二农场种畜站劳动。他在散文中写道:
我们农场的《场志》上记载,最早开发建设我们这个北大荒第二大农场时,是老场长带着一百多人的原铁道兵某师一个警卫连,押着三千多名劳改犯抢通的虎宝公路(虎林到宝清)。
为什么叫抢通?因为他们是从冬末的三月进入荒原的,要赶在六七月份夏季的汛期到来之前在沼泽地即荒草甸子里修出一条百余公里的路来!
所以如果尊重历史,应当承认,在建设北大荒这个事情上,劳改犯们也是有贡献的。另外还加了注解:
据《场史》载:
一、1956年3月,铁道兵九师警卫连等部160余人带领3000余名劳改犯开始修建虎宝公路。
二、1957年3月,省公安厅同意我场对内称第三劳改队(有劳改犯2629名)。
三、1963年6月,农场将劳改犯人和新生就业人员全部移交省公安厅。
郭小林我只文中相识,后来我才知道我俩都是南泥湾三五九旅的后代,也许有共鸣点吧,他的散文勾起我的思路。
凭我妈妈赵英华生前的讲述和我学生时代的回忆把零星记忆写成文字,写一写这支改造队伍中一些人的片段…。
建场初期的八五二农场对外全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八五零貮部农场 ”。
是1956年6月1日,王震司令宣布成立的北大荒军垦农场。
对内则称:“黑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改支队”。
场部先设在爸爸黄振荣、踏荒在军用地图标写的“曙光镇”上(现称:老场部或种畜站),后搬到王震司今员选中有白桦林的“南横林子镇”中。
清晨,在场部地区刚搭起的马架子门前,迎着完达山升起的太阳,朝鲜战场归来的铁道兵司号员吹起了起床号。
随着军号的召唤,有两支队伍按号令起、卧,工作,学习,开始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按部队习惯出早操时,两支分别跑操的队伍引人注目:一支穿黄军装的队伍是铁道兵转业官兵队伍。
另一支穿蓝衣服的队伍,则是被监督改造服刑的劳改犯人。
两支队伍喊的口号前头喊得不一样,黄军装队伍往往喊的是:“开垦荒原,新建家园”。
蓝衣服队伍往往喊得是:“劳动改造,悔过自新”,结尾都是一样:“一、二、三、四”。在劳动时,两支队伍喊的劳动号子嗓音南腔北调,但都喊得震天动地。
这里要说的这些犯人,和分散在农场分场、连队、林场、水库的犯人是一起的。他们一批从江苏省由闷罐子专列押送到农场的。(其中有一原国民党少将,到农场后不久,又押回江苏)。
当时来了六个劳改大队犯人,多为政治犯,也有一些经济犯。我方公安军押运犯人总指挥周传芳(此人后任红兴隆管理局钢铁厂副场长,己去世)。
随后,押送人员和六个劳改大队,均留在农场内。
公安军看守的军装改为警装。犯人的衣服仍是蓝色衣裤,后来陆续押来的犯人衣服变成黑色衣、裤。当时犯人没有统一的囚服,为了区别后来的支边青年,犯人的蓝、黑衣服外,有白线头缝制暴露在外,以示警示此人为犯人。
那时犯人都要外出劳动,重刑犯外出劳动,有带枪武警看守。并划有警戒线,。
轻犯表现好的,两人以上结伴劳动,互相监督。当年看押所,随着农场的发展,住所有所变化,犯人从曙光镇马架子,搬进南横林子镇自建的拉合辨草房,然后又搬进自建的土坯草房。
看押所内,有犯人住所、食堂、图书馆等,没有铁丝网封闭。
室外有电线杆上电灯照明,周围有武警昼夜站岗和巡逻。
我和同学课闲时,看押所的图书馆是我们这些学生常去看书的地方。
图书管理员是一个在押的犯人,照看着图书,对我们挺好。
他双手从手腕以下全没了。还留过我们吃他从看押所食堂打来的饭菜。
他因没有双手,在一个匙子上,捆一个布做的园套,再套在右手腕上取饭菜,送到嘴内咀嚼饭菜。
我们只乘他不注意我们时,偷看他双手一眼,从来不好意思问他的双手那去了。
后来我们家人知道了这件事,规定只许看书,不准吃看押所的饭。现在看来,家人怕犯人在饭中下毒、做文章,也是有戒备之心的。
到总局后,拜读了垦区作家郑加真的有关文章,才知道这个犯人姓熊。
他爸爸是我军一个高级将领,建国后被打成反革命。熊犯人当时在部队当军官,因不满发表一些言论,被检举批捕入狱。
在农场监所又因碎事和某看守争吵。
为此,某看守在监所旁把熊犯人和一棵树捆在一起。招到熊犯人进一步辱骂…。
某看守赌气自己下岗睡觉,忘记解开熊犯人被捆的绳子,熊犯人在冬日雪地上冻了一宿,冻坏了露在外面的双手。
在医院,熊犯人又拒绝医生治疗双手,最后无法治疗,而被锯掉…。
郑加真在书中写道:“后该犯人刑满送回南京,不知去向…;后经组织审查,熊犯人父子俩入狱都是错判案件”。
在随后来农场的犯人中,有一个天津杂技团全团犯人,据说是集体贪污入狱的。
来农场后,为了活跃农场文化生活,做到物尽其用,人尽某才,农场除有文艺宣传队演出外,还让这个杂技团四处演出,可谓花样百出。
其中有一艺人,在表演时拿刮胡子双面刀片,切割下一张扑克牌片片边角,以示刀片锋利,然后把刀片一片片放进嘴内,还不断在表演中喝水,说话。
放完刀片后,他再把一个白线头放进嘴内,再慢慢拽出,一个个刀片,就晃晃摇摇从他口中穿在白线中出来了,看的我们目瞪口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人民大会堂等新建十大建筑,要铺地面的木板块。
接到任务后,农场部份转业官兵、部份劳动改造犯人,到炮守营(原归农场管的林业营,现归东方红林业局)不同地点伐原木,然后运回农场木材厂。由上海来的木工师傅破成木板块。
因为当时没有烘干车间,湿木板块分到各家,铺在人睡的火炕上,烘干再集中运往北京。
由于伐木点冬天在山上伐木,地印子窝棚又冷,伙食也跟不上去,去的犯人闹事,停工抗议了。据说还扣压了看管人员。
消息传到总场,爸爸黄振荣要去现场。妈妈赵英华怕再出意外,要让不到8岁的我跟着去。爸爸一句话:“他一个小孩管什么用”,把我留在了家中。
爸爸带着一个通信员,他俩带着一长一短两支枪,骑着马,趟雪奔向炮守营伐木点。和犯人们见了面。
在谈话中对伐木犯人,晓之以情,告知伐木,是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做贡献,并对伙食、取暖等人性化工作进行了落实…。
犯人们承认了错误,愉快地开工了。
随后,爸爸指示看押部门,不要给这些犯人追加刑期,只给领头闹事的犯人蹲小号,禁闭反省,解决了一场很容易激化的事件。
随着国家困难时期到来,场部地区犯人衣服上补丁多了,但是补丁外面还要缝上白线,以示区别。
连续的自然灾害,犯人伙食下降,吃不饱饭,再加上重体力劳动,死了一些犯人。场部现汽车队后面树林中,埋了不少去世的犯人。还有零星埋在场部变电所旁的树林里。
值得一提的是:我爸爸黄振荣文革中被打倒去世后,造反组织让我们把爸爸也埋在汽车队后面树林里,和死去的犯人埋在一起。遭到我们家的抗拒和反对,但结局,也不让进场部三不管人民公墓,只能孤零葬在白桦林一地。
公理只有人心,后来爸爸坟旁,越集坟越多,成了场部地区新的墓地群,当然这是题外话。
在种畜站连队后面,是省道富饶线(富利屯到饶河),现叫依饶线(依兰到饶河)。在省道依饶线北面小树林中,也埋着不少死去的犯人。由于当时法制观念不强,死去犯人据传说有多人埋在一个坑内,这事被犯人家属告到国务院。
国务院调查组来调查后,死去的犯人被挖出后,才一人坑,重新埋在这片小树林里。
1985年,农垦事业奠基人王震,己是国家领导人。他第十八次来到八五二农场。在风景如画的蛤蟆通水库将军亭里,观望着水中美景,兴致勃勃听水库领导人(当年转业的官兵)介绍:
“王老,这是八五二农场建场初期,您站在这里,指示黄振荣师长,安排转业官兵和劳改犯建的水库…”,
王震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看着这位水库领导人:‘嗯’了一声,没有表态。
这位水库领导人脑子转的很快:“不对,我说错了,是转业官兵建的水库,现在水库己成为鱼米之乡了”。
王震乐了 。
纵观古今中外,对犯罪人就有流放之说:水浒传中,林冲面颊被刺,流放异地。列宁犯错,也被流放西伯利亚。农场建场初期,对犯人不叫流放,叫监押管理,劳动改造。
劳动教养人员在农场简称劳改犯,刑满释放叫劳改新生,留场工作后叫新生就业人员。
随他们身后来的家属、子女,在其不同时期的称呼尾部冠上家属或子女两字。
家属农场给安排工作,子女到上学年龄安排上学。
在我上小学的同学中间,就有不少这样人员的子女,他们在我们印象中,没有被视为另类人群的。
1963年,劳改犯和新生就业人员移交给省公安厅,送往北安地区改造和安置。他们的子女、我们的同学,和我们告别后,也随父而去。
只剩下死去犯人的墓,仍留在树林内。日久天长,有些墓,后来被亲人挖开,把尸骨带走。有些墓下沉,消失在黑土层内…。
中苏关系紧张后,从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的兴凱湖劳改农场中,内迁八五二农场一些新生就业人员和他们的子女。
这些人有些真正犯过罪,有些是冤判的,还有一些错打的右派,统统被打成另类。
在农场时,我曾开车载农场组织部人员,到四分场某连队给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官,上过黄埔军校,从兴凱湖农场内迁的人落实政策。
当时此人正在连队地号内放羊,闻信后急奔回家。全家高兴之及,给我们去的人,每人冲一杯糖水表示感谢。此人以前学过机械,被农场安排到总场汽车队,当副连长,直到退休。
写到这里,我只想沉默不语,但和郭小林同感,还想说几句:
在八五二农场初期,来的这支特殊的队伍中的劳改犯,不管是否有罪或没罪,他们在农场开发建设上,在管制劳动下,有苦有乐,尽了力,是做出重要贡献的。
(杂文有感写成于2012年1月31日,还在春节期间,和节日气氛不太协调。但我只是试想还原农场开发史的一段真实,但从来没有公开,以后可能也不便写进历史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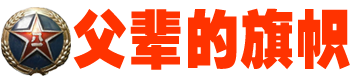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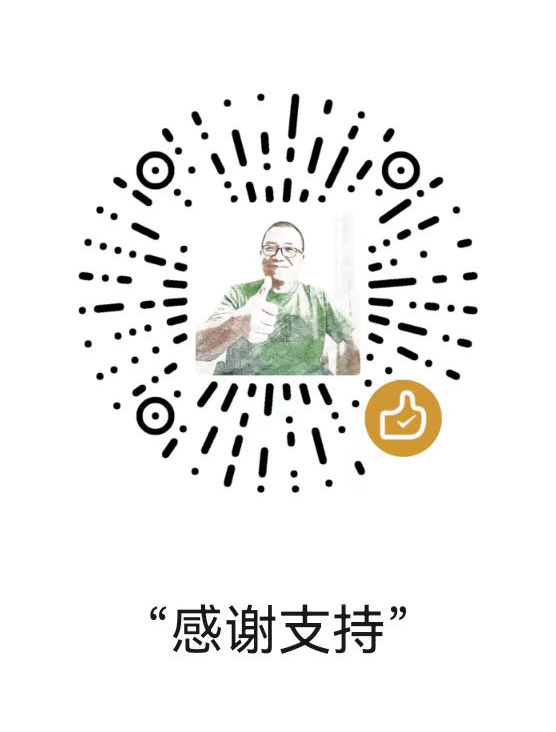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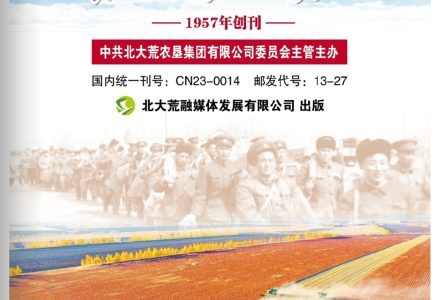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