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庆幸当年自愿下乡时选择了八五八农场。这座农场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创建的。这些转业官兵发扬“南泥湾精神”,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人拉肩扛、搭马架睡草铺,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茫茫沼泽荒野上建起了一座座大型农场。1968年我们下乡的时候八五八农己经是一个拓荒20余万亩,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的机械化国营农场。现今大力提倡的北大荒精神,就是这些转业官兵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坚韧意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下乡就坚定地把这些转业官兵们作为学习傍样,处处事事跟他们学,一心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做点贡献。
我们十八连共有十三名58年转业官兵,包括连长刘天银中尉、前任指导员张文德士官、后任指导员李子敬下士、一排长张志华士官、三排长杨金德士兵、四排长刘其友步校学员( 准尉) ,还有作为普通职工的陈光伟中尉、王绍才中尉、夏志忠少尉、陈金友士官、候世川中士、王者兴士兵、孙都军士兵。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军官、老战士带领,18连象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老连长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这些转业官兵就像知青的兄长,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是那样温馨美好。
老连长刘天银的事迹我和其他荒友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本文就不讲了,主要讲讲其他转业官兵的事迹。
我们一排58年转业官兵最多,有八人。我先后当过一排的榨油二班和搬运三班的班长,这些都是转业官兵陈斤友和王者兴主动让出来的,为的就是让知青们担当更多的担子,经受更多锻炼,更快成长。我当过班长的这两个班里有过六名58年转业官兵。除陈金友和王者兴是老班长协助我工作以外,还有陈光伟、夏志忠、王绍才、孙都军,都是班里的“兵团战士”.他们中一共有二位中尉、一位少尉、一位士官、两位列兵。老八五八农场转业官兵号称有三大才子、四个小鬼,三大才子全都在我的班干过。陈光伟是大学文化,部队的马列主义教员,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属于理论、外语才子;夏志忠高中文化,曾撑起大半个副业队,生意场上的鬼点子又多又精,属于商业才子;王绍才高中文化,原农场宣传部副部长,出口成章广引马恩列毛,下笔千言不离唐诗宋词,是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家才子。夏志忠因诡计多端、随机应变,还被称作老农场四个“小鬼”之一。我们班真可谓人才济济,我这个班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经得意地自称是“全连级别最高的班长”(见照片)。尽管三个尉官在57年都被划过“中右”,其他士官和老兵平时的话也不多,可他们都是农场的创始人,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在和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学习的日子里,他们通过一件件小事、每日每时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有这么多的好师长在身边带路又身处艰苦奋斗的环境,我的进步在18连知青中总算是比较快的,年年都是五好战士,还被评为连里青年标兵。
薛克建:无怨无悔献终身——记我们班的转业官兵
做水泥管了。和我共事最长的当属陈光伟,他和我一起扛过麻袋、榨过油,相处4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关在老加工厂的“牛棚子” 里。1957年他在部队曾被错划为右派,反右结束时又被改为“中右”,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文革中农场的造反派搞极“左”,硬是把他当成“地富反坏右揪”了出来,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我们知青刚到加工厂,领导就把看管“黑帮”的任务交给我们,说是先让我们上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实际上是老职工都不愿干这缺德事推给了我们。老连长一直都是看不惯极“左”那一套的,那几年造反派总想抓住老连长的一些话和事把他打倒。可老连长战争年代是一级战斗英雄,垦荒时又是模范,造反派实在找不到理由整他。没想到这次老连长竟安排我和里一个哈知青孙锦国值夜班看“黑帮”管”“牛棚”,让小童白天看管“黑帮”领着干活。这叫我们俩大吃一惊。我父亲那时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关在“牛棚” 里,孙锦国的父亲因“特嫌”同样被批斗。我俩早就如实的向领导汇报过,老连长也了解,却还这么安排,一定是有用意的。我俩坐在宿舍里捉摸了好长时间,找出两个理由:一是我们俩的父亲遭遇和关在后边小黑屋的“牛鬼蛇神”一样,连长相信我们一定会善待他们,绝对不会象副业队造反派那样打人;二是信任我俩,同样也是在告我俩“牛棚”里的也是好人。
关“黑帮”的小屋就在我们宿舍后边的一个茅草房里,里边住了三个人:陈光伟——“右派”。褚九山——“地主孝子贤孙”,杨吉业——“富农孝子贤孙”。原来造反派们嫌农场的地主富农太少,就连地富的儿子也都当地人抓,根本就不管什么“不唯成份论”和党的政策。当时可想不到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我的班里的成员。当我听说这里有一个解放前的大学生,还是部队的马列主义教官,我就好奇地仔细观察了一下陈光伟。他四十多岁,细高个,脸色略黑;尽管瘦点儿,还算健壮;高鼻梁带付眼镜,如穿上长袍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学究了。(见照片)此人嘴唇略厚,一看就是个有知识能说会道的人。
我和孙锦国值班的头一天晚上就听说:原来的看管人员一到晚上就在外边把门销上回去睡觉,里边的人起夜出不去,只得尿在屋里。冬天屋里很冷,尿虽冻成冰还是很难闻的。领导交待我俩看“牛棚”时没明确说是脱产,我俩也不想脱产,因此不能整夜守在那里,那明天还怎么干活?所以一到晚上我们就把锁头和钥匙一起交给这几个“黑帮”,让他们在屋里边把门销上。开始陈光伟还不明白,问我俩:“门在里边锁上,那匙钥怎么给你们呢?”我说:“钥匙就放在你们那,起夜时打开出去,回来再锁上。”杨吉业这小子平时嘴就不老实才惹的祸,这会儿而不偷着乐还问我俩:“就不怕我们跑了?”气得我没好脸的回了他一句:“要跑你早就跑了。”
过了两天老连长告我俩:“这些人干活太累吃的又不好,身体要是垮了会影响工作的。我已经告诉他们的家属,晚上给他们送饭来”。这下我和孙锦国明白连长让我俩看“牛棚”的意思了。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的家属就来给送饭了。杨吉业是老婆一个人来的,褚九山的爱人是党员不便来,让儿子送来的。只有陈光伟是全家都来了。他爱人是“山东支边青年”,带着姑娘和儿子一起来看他。送什么吃的,我俩从不检查,但可以断定陈光伟的饭是最多最好的,看来他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亲人相见的情景,一下子就想起我下乡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和父亲见面。那是我找了很多人、多方努力,看管我爸爸的造反派才同意我去“牛棚”见父亲20分钟。造反派一声吆喝我父亲走了出来,先向造反派弯腰“请罪”,然后和我草草谈了一会儿。看着老父亲的样子我真是悲愤交加。现在他们的相见勾起了我的伤心之处,顿时两眼发酸眼泪差点没有掉出,好在是晚上谁也看不出来。我看了一眼孙锦国,他的眼睛小天又黑没看出有什么变化,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难受。
农场的造反派一直认为老加工厂总不召开批斗会,“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加工厂的那两个造反派也认为是老连长有问题。证据之一是他曾说过:“一开会他就头痛”。可他俩人少势弱,在加工厂根本就掀不起妖风来。副业队的造反派早就想插手帮一把,就提出要与加工厂联合开搞批斗会,目的就是想掀起一股妖风把老连长揪出来。在当时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老连长必须应付一下。于是就把联合批斗会的事跟我们的知青老大哥张广兴说了,让他准备一下批判内容。老大哥很敏感,副业队原来每天只在自家门里批斗“黑帮”,这会儿提出联合召开批斗会这里肯定有问题。老连长告他说“是针对我来的”。张广兴提出得反击他们一下,老连长说“隨他们去我不怕”。老大哥回来就与知青们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都对副业队造反派的做法十分反感。最后大家觉得要变被动为主动办法只有一个:表现得要比副业队造反派更狠更“左”。首先先得狠批已被揪出来的加工厂“黑帮” ,来抢占批斗会的制高点,一举掌握这场批斗会的主控权。老连长听说我们要批斗加工厂的人,就先找了个理由把陈光伟支开,保护起来。老连长战争年代是机枪连付连长,他曾讲: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死在他枪口下的敌人数都数不过来,同样机枪阵地也是敌人炮火打击的重点对象,敌人一阵炮火复盖过来战友就倒下一片。有一次战斗下来,全连一百多人就剩几个人,因此他对活着的战友的感情很深。虽说陈光伟和他不是一个部队的,可对战友的关怀是一样的。批斗会一开始,加工厂知青抢先上台,大喊一声:“把加工厂的牛鬼蛇神带上来”!童森瑞和关汝臣就把诸九山、杨吉业押了上来。可随后张广兴率先发言,滔滔不绝把阶级斗争的意义说得头头是道。口号喊得响亮有力,远比副业队造反派们有理论有水平,一下子把他们的气焰压了下去。那些想把矛头对准老连长、攻击加工厂右倾、不抓阶级斗争的人没找到任何一点理由。可是我们这帮小青年一“左”起来也刹不住车了,趁势又把引来外鬼的加工厂造反派张某某也打成反革命押了起来。把造反派押起来,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情,张某某也很不服气。叫他跟“黑帮”一起排队他不干,非要站在边上走当领队。陈光伟个高是个排头,我们就叫他陈紧跟在张后边走,不管他到那都着排队跟着他,不愿排队也得让他排着队走。张不听话,小童就让他上一边撅着低头认罪。他说:“我是造反派不会撅着”小童就说:“那你怎么会叫别人撅着低头认罪呢?”随后一摆手,“杨吉业你过来!给他作个示范。”杨吉业这小子马上走过来,大弯腰120多度做了个样板。我也想让陈光伟也出出气,我叫陈光伟也给这个昔日造反派作个样子,教教他。老陈也很认真的来了一个90度标准动作,我想他俩做示范时心里一定会偷着乐。张某某就是不弯腰撅着,小童就叫杨吉业、储久山按他的头,教他怎么做。副业队是造反派按夏志忠等“黑帮”的头,可加工厂却是“牛鬼蛇神”按造反派的头。这叫农场和副业队的造反派都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加工厂变了天。只是此时现役军人已来农场组建兵团,才没敢来加工厂兴师问罪。这可能就是副业队和加工厂合并组建十八连以后,张文德指导员不喜欢加工厂的知青,临走时唯独不与哈尔滨知青照象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家工厂知青一直看王正亮副连长不顺眼的主要原因。这次批斗会搞极“左”肯定有负面影响。储九山、杨吉业后来知道了因由,原谅了我们。可副业队的知青们和老职工一直对小童、小关的行为有看法,我和孙锦国那会儿不能出头反而成了好人,这可真是难为小童和小关他们俩了。
当时边境形势越来越紧张,打仗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1969年元旦前后要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进行到连队一级,基层按照毛主席“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指示开始“落实政策”,没有多大问题的“牛鬼蛇神”纷纷被解放出来。陈光伟、储久山、杨吉业也都“摘帽”,成了我们班的兵团战士,大家朝夕在一起干活学习,接触多起来,也开始工农个深入地相互了解了。
我发现陈光伟干起活来和被改造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样抢着干,叫干啥就干啥。学习时总是小心翼翼,发言时决不离开“两报一刊” 的说法。他的发言总是慢条斯理,分析问题有条有理逻缉性强,不愧是大学生、马列教官。那时农场的大学生很少,可能只有两个人,我们班就有一个,还是解放前上海的大学生,全农场只有他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听说读写。了解到这些,我开始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他身上有很多的迷吸引我。他上的什么大学?为什么参军的?又怎么成了“中右”?怎么来北大荒的?后悔不后悔?……。有些问题可以在班里学习时问一问,有的就只能找机会慢慢了解了。
我在班里学习的时候有意地问了陈光伟一些问题,我问他:你家庭生活不错又在上海上大学,据说上海人不能吃苦,你怎么想起参军呢?他讲:他生在福建,小时候在厦门,那时到处都有因贫穷饿死的人,还经常看到日本浪人欺侮中国人,对旧中国政府对外软弱对内欺压百姓非常不满。解放战争时期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毅然投笔从戎参军报国了。其实他只说了个大概没敢细讲。我又问他怎么来北大荒了呢?他讲:在部队说错了话,犯了错误,到北大荒来锻炼改造的。还是讲个大概就是不敢细说。
可说起来到北大荒后的艰苦奋斗来,他就和其他转业官兵一样滔滔不绝了。他讲:那年冬天,卡车把他们这些转业官兵拉到了大雪茫茫一片的荒野地,领队的人下车,用手一指这旷无人烟的地方说:“下车,到家了。”大家赶紧下车,砍树枝搭人字架,割荒草苫上去就成一个小草屋。没有床就割树枝先在地上铺一层隔潮,再割一捆捆草铺在上面搭上地铺,这就是他们到八五八农场后的第一批“建筑”(见照片)。当时就连这种草房子都不够住,大家还得挤着住。睡觉时还得一个人头朝前另一个人头朝后,不然挤不下。单薄的茅草房根本抵挡不了北大荒的寒冷,头朝前睡的冻脚,脚朝前睡的冻头。北大荒有几怪,其中之一是“吃水用麻袋。”他们喝水就到水边用镐铇冰,再用麻袋把冰抬回来烧水喝。菜几乎顿顿都是吃冻白菜和冻罗卜,能吃上冻土豆就算改善生活了。难得吃上点肉。春天开荒种地时没有拖拉机就用人力拉犁翻地( 见照片4)。那个时候是他们这些转业军人仍然在预备役中,是种地的军人。没有播种机他们发明了“裤插机”:用裤子装满种子捆住裤腰放在肩上扛着,两手把住裤腿角控制流量边走边播种,一不小心撒多了,春天地里会鼓出一个个小芽苗包来。到了夏天,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蚊子和小咬多得无法想象,一群群蚊子飞起来就象一团团的黑烟,一片片小咬飞起来雾蒙蒙一条一条的。我们下乡的时候听说蚊子和小咬已经少多了,可我们还曾创造过一巴掌拍死40只蚊子的纪录呢。小咬出来的时候,为了防它钻进头发里咬人,我们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自称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只露在外边看路和通气的小脸,手里还得拿着一棵小草,在眼前晃来晃去驱赶蚊虫,我们开玩笑叫它隐身草。还学崂山道士互相问:“能看到我吗?”你要是说:“看不到了”,对方就会装作“隐身人”掏你兜里的东西。我们经历过大量蚊虫的叮咬,就能够想象出建场初期时蚊子和小咬多的可怕程度,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就是现的北大荒人也只能想象几分。这些困难,每一项对转业军兵都是很大的考验,需要坚强的意志韧力才能去克服。
说起当年艰苦奋斗来,陈光伟曾深有感触地说:“农场创建时的第一批连长、指导员过早地都死光光了,都是累死的。”他的说法,《八五八农场史》也有详细的记载:农场的早期领导人,老红军萧天平、曾柯等人,60年代病逝时都只有四十几岁。在战场上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垦荒的战斗中。虽然他们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英年早逝了,但他们始终是我们知青心中最可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时间一长,大家相互有了了解,有了感情,说起话来就少了几分戒心。陈光伟开始叫我薛班长,慢慢的就亲切的改叫小薛了,可我一直尊称他为老陈。平时大家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说,后来发展到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老陈也有了笑声。他的笑很有特点,一笑就脸微微向上:“哈、哈、哈哈!”不属于扬脸大笑,可算是扬脸中笑,笑得那么朴实又那么尽情。慢慢地老陈也愿意和我们述说他的经历了。他在福建长汀读高中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1945年上了江西南昌“中正”大学。不久他就对国民党腐败政府失去了信心,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总登记时,他拒绝登记,退出了“三青团”。在地下党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当时他热情高、敢出头,47年夏初大学生组织的反内战逰行,他是撑大旗的两个人之一。1948年这所大学发动“争自治、反迫害”运动,吓得反动校长林一民离开学校,系级联合会控制了学校大权,他是七人主席团中的一个。到了暑假学生散了,反动军警进入学校,他和九位同学被开除学藉。当时还有一个“特刑庭”专门抓捕镇压学生。解放后,南昌历史博物舘中保存着一份当时特务要抓捕的三个学生的名单,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蒋介石的中正大学里参加革命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他跑到上海,又利用家庭关糸进了教会学校沪江大学。一解放,他没等完成学业就积极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见照片)。刚解放时部队里大学生很少,他被分配到总后勤部西南军区重庆办事处,任中级马列主义夜校理论教员。听他讲课的全是少尉至少将级军官。在“反右”的时候,他提意见说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还有他看到有些中央领导人出国回来,在重庆接风宴上吃小乳猪,不少人还带上四川买的大皮箱和籘器家俱,从水路运回北京。他们私下议论,认为共产党人变了,要学国民党了。就因为这些话,他成了总后勤部第一批右派,过后又改成了“中右”。其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今天看也没什么错,老陈的话是指教育、文化艺术方面,你在没成为内行之前是没法实施正确领导。领导得尊重科学,如果你成了内行再说你不能领导,那才是错的。我们党为使干部尽早成为内行,曾在58年把大批老干部下放基岛层锻炼。象商业部副部长胡立教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当地委书记;黑龙江省副书记于杰到嫩江地委当专员;副省长于天放到牡丹江当专员;我父亲也从省总工会到了基层企业锻炼。这些说明我们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老陈的话正好和一些著名右派“攻击党的言论”一样,被人抓住上纲上线。老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他诚恳地告诉我们这些小青年,当年他说这些话,都是因为肩章上少给了一个“豆” 闹的,让我们千万别学他。可我心里却在想:老陈提的意见,比如批评某些干部腐化,并不是全无道理。为什么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免的对待这些意见呢?
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撤消的时候,老陈被分配到了北大荒。对此老陈毫无怨言。他说自己这个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需要到最基层改造锻炼。何况那么多老连长这样的战斗英雄和老红军、老八路都能来,自己就更没什么说的。他和其他转业官兵们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看见过没有饭吃饿死人的情况;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人多地少粮食还是不够吃的,所以能够理解国家为了解决吃饭的大问题,动员大批干部到农村边疆艰苦奋斗。当年十万转业官兵开赴北大荒时的口号就是:“开垦北大荒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就是他们开赴北大荒的目的和决心。(见照片5)。
老陈在文革前是农场总库主任。那时各种物资、另件、粮食都在总库里,兵团组建后物资和另件库才从加工厂划到团部物资股。那时他从不坐在办公室里,成天就象一个搬运工什么活都干,难怪后来在我们搬运班扛起麻袋驾轻就熟呢。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级派来的社教工作队,看到他在粮库晒场上干活的表现,在首场宣讲时就大力表扬他,说他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好典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我眼里已经是个地道的劳动者。他在被管制期间,他曾跟“杂家才子”王绍才斗嘴打赌,成功的扛起两麻袋玉米(340斤)从粮库里边走向大门,赢了五毛钱。在班里干起活来他总是抢在前面,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比青年人少干。按说大学生是五谷不分的,可他家的园子收拾得有条有理,黄瓜、西红柿、蔬菜长的一点儿不比老农的差。有一次在连里的地里收大葱,他捆起大葱比班里赵焕九的父亲干得还快。小赵的父亲是当地老农户的队长,他看老陈这个知识分子干得比他快,就说了些怪话。老陈笑着说:“我不跟你吵,我只要抓把大葱朝天上一扔就行了。”我马上问老陈:“为什么说扔一把大葱就行了呢?”老陈笑眯眯地说:“山东人见了大葱就不要命,你一扔大葱山东人就不跟你吵了,全都去抢大葱去了。”我们几个知青一听都大笑起来。老赵是山东人,他马上大喊“这小子埋汰山东人,这儿有没有山东人,赶快收拾这小子。”地里很多老职工都山东人,全跑过来把老陈实实在在地收拾了一顿。我也是山东人,也情不自尽地参加了进去。老陈笑着躺在地上求饶,活脱脱像个老农民。
老陈他从大城市来到北大荒这么艰苦的地方,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怨言来,每天总是那么认真的做事,与同事们说说笑笑,有时还会有些童趣。在班上老陈和老夏这俩大才子遇到一起,经常吵嘴掐架,吵完一笑从不记仇,好象越吵关系越好。有一次我与老陈、老夏及上海知青袁晓农四个人一个班里榨油,中间休息时我把话题又引到了这两位转业军官的过去上。老陈和老夏都是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的战友,老夏是搞部队营房建设的,老陈是马列主义教员,这两位“中右”加才子碰到一起互不服气,常常发生争执,我们知青都愿听他俩吵架,既热闹有趣,又长见识。每次我说“我们知青应好好向你们转业官兵学习”时,老陈总是谦虚地用他的口禅说:“不得了!不得了!我不够格,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同样是需要改造和锻炼的,没有资格教育别人。”“不得了!不得了!”这是老陈碰到重大问题时爱说的话。他说的是心里的话,一直到最近,已经86岁的老陈还讲过:“我到北大荒是接受改造和锻炼的。”可老夏听了却反驳道:“你一贯不说实话。”老陈问:“我怎么不说实话了?”老夏说:“批斗你的时候造反派问你有罪吗?你头点得象小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那么我现在问你罪在何处?你现在还认罪吗?你要是认为没罪了是不是在说假话?”老夏连珠炮似的发问弄得老陈想了半天才回话:“那个时候你要说没罪,能过得了关吗?我那叫策略,不叫说假话。”老夏不依不饶:“那叫没骨气!”老陈一听乐了,跟我和袁晓农说:“老夏可有骨气了,副业队的造反派批斗他的时候就是不认罪,造反派把他脑袋按下去叫他弯腰认罪,可他就挺着脖不弯腰不认罪。人家使劲把他脑袋按下去,稍一松手他就挺起腰直着脖子喊:我不是反党份子!再按下去就再直起来,因此挨了不少批斗和体罚。最后让造反派给带上高帽游了街,他老夏还不是只好带着高帽敲着锣,一路喊着自已是反党份子吗?咱老陈态度好,就没被游过街。不过夏志忠还真是有点骨气。游街的时候,敲锣还能敲出个点来,‘镗镗以镗镗’,象耍猴一样热闹。”老陈的一番话说到了老夏伤心处,坐那沉默了起来。我问老陈:“咱团部就这么大点地方在哪游的街呀?看的人多吗?”老陈讲:“就在团部十字路口那儿来回走走。中午的时候,还有几个人看热闹,都是被他的锣声吸引过去的。”袁晓农正听得入了迷,一看都不讲了,就用上海话说:“再(港)讲点,再(港) 讲点。”老陈见老夏不吭声也就不再说了,他也不愿多讲那段伤心的事。
夏志忠(见照片)不但和老陈都是老农场三大才子之一,还是老农场四大小鬼之一,被老陈揭了老底总有些不甘心。机灵鬼就是机灵鬼,第二天老夏把我叫到一旁说:“你别看老陈挨斗的时候,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实他这个人特别要面子,最怕出洋相,臭知识分子都这个德行。不信你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组织咱们班搞一次军训,咱四个人穿着裤头光着膀子到团部十字路口跑步,看看老陈怎么办?他脸皮薄了肯定不干,不信咱们就试一试看。”小鬼就是小鬼啊!小鬼再加上才气鬼主意和点子就是多。老夏这明摆着就是要借我的手报复老陈,也想让老陈在团部十字路口出把丑。我这个人生性好玩好闹,连声说:“好!准能让老陈难看。”那个年代工间休息不叫休息叫学习。我就利用学习机会跟大家说:“今天的学习改学军事,咱们一起排队到团部十字路口跑上一圈练练队列。”夏志忠马上响应说:“我打头领跑,薛班长断后监督。”老陈一听就知道这是“夏小鬼”出的鬼主意,就说:“不能只穿裤头光着膀子跑吧?穿上衣服去跑吧。”老夏赶紧说:“又不是下班穿什么衣服?班长不是说了吗,利用学习时间军训。大夏天外边又不冷,就这么跑!你怎么这么多事呢?”老陈一看不好就不与老夏理论,直接对我说:“小薛,光着身子中午在人多的地方跑步多不雅观,熟人看见就太丢人了。要是让孩子和家属看见就更不好了,会让他们在众人面前面子过不去的。”老夏马上就开始借题发挥:“什么臭老九!只顾面子不顾里子,怕字当头怎么上战场啊?”我听着他俩的争吵一时没了主意,我答应过老夏一定跑一把,可又觉得老陈说的有理,玩笑开开可以,开大了就不好了。这俩人都是我的老师我都得尊重。老夏是原副业队领导,可老陈从“牛棚子”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我心里的天秤慢慢倒向了老陈,就跟老夏说:“我虽说是班长可在你们俩面前,还是个小兵蛋子接受再教育的小学生,老陈他不跑我也不敢强迫,算了吧。”老夏一听我不跑,只得放弃自已的主张。可机灵鬼脑袋一转鬼主意就又来了:“不跑可以,但是得罚!”老陈一听可以不跑了,就高兴的说:“认罚,认罚,我认罚。”老夏马上说:“明天空油吃午饭的时候,你在家里给我们三人带一大碗炒鸭蛋吃。”老陈立马表态:“没问题。”就这样两个大才子结束了第二回合的“争斗” 。
第二天老陈真的带来一大碗炒鸭蛋。说起来也很怪,别的地方农村都爱吃炒鸡蛋,可农场这个地方的人爱吃炒鸭蛋,这可能因这里的人都操着南腔北调,从山南海北四面八方来的,也可能这里水多养鸭子多的原因,所以口味也就与黑龙江本地有所不同。老夏他是四川人,我没去过四川,可能四川人爱吃鸭蛋,老夏才要的炒鸭蛋吧。要是我肯定会点炒鸡蛋。老陈家里炒的鸭蛋也挺好吃的,班里别的老职工家我都去吃过饭,可从没到老陈和老夏家吃过。不是我不想去而是他俩不敢请,生怕有人说是右派争夺小青年。吃着老陈家炒的鸭蛋还堵不住老夏的嘴,他一边吃着一边不怀好意的看着老陈说:“真好吃!太好吃了,”还一个劲的问我和袁晓农“够吃不?好吃不?”我俩一边吃一边说够了,好吃。老夏就问:明天再来一份怎么样?老陈气得也不理他。如果光是我和袁晓农,他再来几份都会心甘情愿,这里有个老夏再来一份他是不会干的。
老夏吃完炒鸭蛋还当着老陈的面前走来走去,哼着小曲,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继续气老陈。老陈坐在那假装不生气,但眼睛一直盯着老夏看着他表演。忽然他看见老夏拿了一张纸走了出去。老陈太了解老夏了,知道老夏有按时大便的习惯,这会一定是去外边的厕所了。那个时候没有室内卫生间,在外边挖个坑再盖上小木房就是上好的厕所了。我们油房的厕所是在一个小水坑边上建的木板房,夏天雨水灌进去大便得小心点,一不小心脏水就会溅到屁股上。那几天下雨,粪坑里早已灌满了水。老陈一见老夏出去了就向我摆摆手跟了出去。我一看大戏又要上演,也跑步跟了出去。老陈在路边捡了半块砖头,我马上就明他要干什么了,也顺手拾起一块石头紧跟在后边。我俩跑到厕所的后边用力把砖头扔进厕所的水坑里,只听到咕咚!咕咚!两声响,四十多岁的老陈象个孩子一样乐得跳脚往回跑。我们一蹦一跳兴高彩烈地跑回来,一进油房就装作没事似地坐在烘豆皮的坑头上。一会儿老夏走了进来,我们以为一进门他就会大发雷霆,责问是谁干的缺德事,溅了他一屁股粪水,我俩再哄堂大笑,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想到老夏进门就象没事一样,也不看我俩一眼就走进浴室里洗了一洗,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反而坐在我俩身边等着开工。老夏这一招反到把我俩镇住了。这个夏志忠也太鬼了,他不吵不闹是不想让我俩再看他的笑话,不发火发怒是想要显示他多么有修养。这样一弄他倒占了上风,成了有修养的君子,我俩却成了损人不利已的小人了。这时老夏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是说:“好啊!你和老陈都是老加工厂的,你偏心向着老陈。”而老陈的表情好像是在说:“我的鸭蛋你老夏也不是好吃的呀,吃了也不能白吃,得付出点儿代价。”就这样老陈和老夏的第三回合也就结束了。
我们班的知青都十分爱看两大才子的争斗,从中能感受到他们在困境中的幽默,己是中年的他们的童趣,还有各种鬼主意。他们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哲理也感染了我。每天我干的活都是连里最累的,但一天下来我总是快快乐乐,到处找有趣的事干来找乐子。在十八连里我是出名的爱闹和淘气。天津知青程雨泉也是个淘气包,工作干得也非常好,可他不会耍滑,淘得没情趣,老是挨领导的批评。我跟老陈老夏这两个才子以及老职工隋丕英、靳洪贵学得也爱淘气,但总是适可而止,淘得有情趣,很少挨领导批评。我常对程雨泉讲:“老天真不公啊,谁叫我的老师水平高呢。”
说起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这段历史,我觉得人们对这段丰功伟绩评价和歌颂得还很不够。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穷二白,粮食总是不够吃的,吃饭问题一直是困挠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70年代回哈尔滨后我在省粮食部门工作过。那时就是赶上丰收年景,全省也会有一些地方因为没有存粮又一时调拨不及而缺粮。直到1975年,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才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用占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解决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当中北大荒的贡献功不可没。1975年黑龙江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亿斤,现在是1300亿斤,其中北大荒垦区就有600多亿斤。转业官兵们开创的垦区今天的粮食产量已经是1975年全黑龙江省粮食产量的两倍多,相当于多了两个黑龙江省在打粮。黑龙江省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是全国各省之中提供商品粮最多的省份。北大荒垦区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转业官兵创建的北大荒垦区对这个奇迹的贡献最大。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垦区的转业官兵们心系全国人民困难,无私奉献把整列整列火车的粮食输往全国各地。八五八农场那时每人每天只吃四两八钱(16两1斤)粮食,勒紧裤腰带还得干重体力劳动。老陈讲过,那个时候他们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跑到地里象老鼠和野鸡一样,扒开大雪捡掉在地里的谷粒来充饥,甚至到牛圈马号四围去转转、看看有没有谷粒可捡,就是发现牛粪里有玉米粒也捡回来洗洗吃,那个冬天,浮肿的极多,有些人连饿带病而死。这是何等的精神哪?这就是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老陈后来调到团部中学,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英语教师,为提高边疆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奉献了几十年。十八连以老连长为首的转业官兵们,对我和连里知青的影响都很大。那时我们二十岁左右刚刚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在这些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很容易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这就是现在为什么18连的多数知青对下乡经历的体验与许多人不同的原因。转业官兵们艰苦奋斗创业的经历,坚韧不拨克服困难的毅力,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当年的我们,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老连长的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陈光伟坚定诚恳、自我改造的意识,夏志忠坚持真理绝不低头的硬劲,班里最不爱说话的孙都军叫干啥就干啥的劲头,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都不曾听过他们有什么豪言壮语,却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事。
我知道现在社会上对知青这段历史有很多的说法,说好的不多,否定的多,甚至还有人不承认北大荒知青为边疆做出过贡献。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的一次错误运动,“文革”错了,所以下乡也就全错了。我看这种说法不符合真实历史。“文革”让上山下乡运动变了味,但它不是造成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中国太穷。那时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不过一、二千亿元,与现在的十二、三万亿元没法相比。那时没有多少钱投资基本建设发展经济,工业商业发展水平也太低,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多毕业学生的就业岗位,国家没基础你让我们去怨谁呢!79年“大返城”知青大批回城后,多数不也是很难有工作、几乎沦为城市难民吗?中年时,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下岗”丢了工作,造成生活困难,这些又该怨谁呢?难道也怨“文革”和毛主席吗?要怨就这只能怨自已生在那个年代。后悔那些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58年十万转业官兵也是全国性的裁军时无法安排在城镇就业才去垦荒的。那时中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不去农村又能去哪里?他们当年的艰苦奋斗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几十年来他们的奋斗经历和精神获得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今天你不管问到那位转业官兵,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对在北大荒吃过的苦无怨无悔。前几天我和孙锦国刚刚去看望过在上海的儿子家安度晚年的陈光伟。谈起往事我又一次问他:“你对去北大荒后悔过吗?”他仍然坚定地回答:一点儿也不后悔。他说,他在中正大学时和他对立面的三青团骨干的同学,后来是台湾著名大学的教授,他们知道老陈的情况后直笑话他。他听了根本不放在心上,说就这样他也不后悔。他的人生两次重要转折,第一次厌恶国民党的腐败而退出三青团、跟随共产党;事实证明跟对了。第二次到北大荒垦荒,是为了全国人民能吃饱饭,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今天回头看,当年的口号“开垦北大荒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并没有空喊,已经完全实现了,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几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献了青春献了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自觉这一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在今天,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这种精神仍然是我们我们北大荒知青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行,祖国的每一次挫折我们都饱受磨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制度,造成我们无法升学又无法在城市就业,只能主动或被迫下乡,根本没有其它选择的权利。我们下乡后在转业官兵的影响下努力奋斗,为建设祖国的北大粮仓贡献了青春。我们十八连知青平均下乡8.3年,比全国知青长很多,但要和陈光伟、夏志中这些58年北大荒转业官兵就差得远了。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熟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名言。如今我们这些北大荒知青也全都年逾花甲了,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下乡那一段经历呢?转业官兵们又一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只要你想到,当国家经济还很落后、需要一代人挑起重担时,我们挺起稚嫩的肩膀扛过来了;那么无论你今天是高官大款、知识精英,还是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下岗职工,你都是创造新中国辉煌历史的一个成员,都可以象老陈他们那样说: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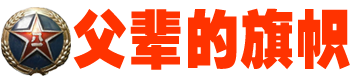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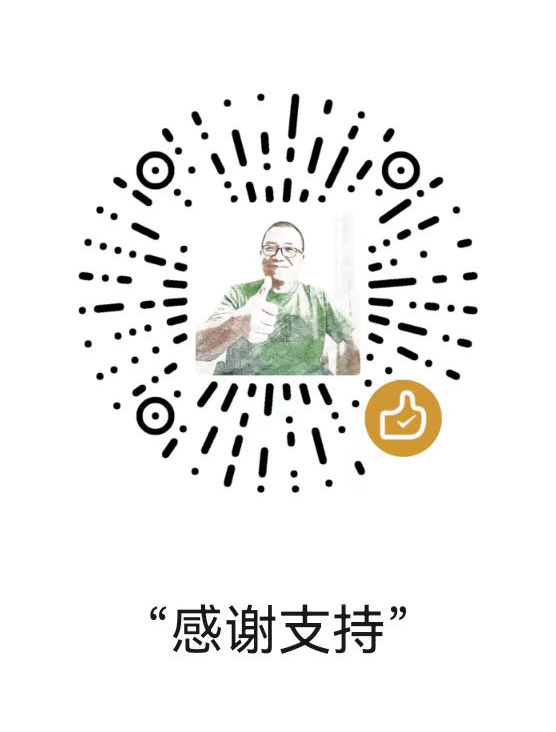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