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北大荒后东北三件宝中人参、貂皮没有见到,只是乌拉草的美妙是体会到了。这里夏季雨水充沛,因而道路泥泞,蚊子又多又大,咬人很痛。白天热夜里冷,温差太大。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对付它们,我们也有了三件新式武器。因而在下放的十万官兵中又流传了这样的歌谣:“北大荒,三件宝,雨靴、蚊帽、破棉袄。”
这里的军垦农场一个连(生产队)要种一、两万亩地,一个农场面积比南方一个县还大。我们农场只有总场部到火车站有一条下雨能走汽车的砂石路,生产队到场部、各队间都是土路,虽然一天也开不过几辆车,但十分宽阔。是用推土机将两边土向中间堆积再用压路机碾压而成的,为了便于大型拖拉机拖着犁耙等大型农具转移地块使用。晴天还好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了,更不要说下了土路进入田间有车辙的田间“路”了。这里土很粘,一脚下去会粘上几斤,越走越重。田间更是能陷进去二、三十厘米深,用力一拨鞋子掉了,一双新鞋这样拨几次也会掉底、散帮。
于是高腰水靴成了一宝,人人必备。商店进一批卖一批,供不应求。一些人就要老家寄来,最受欢迎的是那种电工用的橡胶好底很厚的绝缘靴,一场雨后要穿三、五天。才换上农田鞋,又下雨只好又穿它了。
这里低湿,蚊子特别多,早晚更是一团团地向人进攻,咬的又痛又痒。夏锄时再热也要长袖衣裤,否则裸露的地方会咬得疙瘩连片的。清晨到地头有人去排水沟大便,必须先点一堆火薰烟,否则就要你好看了。有一种比蚊子小得多的飞虫——小咬,成千上万,在无风的阴天或黄昏后围着你的头转,往头发里、耳朵里、嘴巴、鼻孔里钻,咬得你五心烦燥,恨不能跳进水中避难。初去时竟有人过敏被咬感染,头肿得老大,住院挂了好几天水才消肿。太阳升高后天渐渐热了,蚊子、小咬下班休息,这时重型轰炸机牛虻出动了,这里的牛虻比蜜蜂大,咬人又狠又疼。连牛、马都怕它,厚厚的牛皮、马皮都咬得透,咬得牛马屁股上一片血迹。后来每人就发了一顶防蚊帽,它用白布做的凉帽,外围一圈纱布,眼前这一块则是马尾织成的网,可以看清外面事物。早晚蚊子多时戴上它,下面一收口用细绳扎在上衣领子外那就万无一失了。日本关东军军帽后围的一圈布就是防蚊用的。也有人用过防蚊油,但抹一下管不了两、三小时,一瓶只用三、两天,谁用得起呢?所以蚊帽子成了第二宝。
这里夏季中午也能热到三十几度,但早晚不足十度,夜半凌晨天更凉,早上起来得穿上毛衣、背心再加外套。干活热了再一件件地脱,很不方便。这里地块大,夏锄一条垅长的有一千多米,衣服脱在地中间收工了找都很难找。穿单衣又凉,冷风一吹会打寒战。还是部队发的黄军棉袄最为方便。破了也没有几个人去补,脏了也不刷洗,特别是拖拉机手们,棉衣外一层油污像似盔甲似的,下雨都浇不透。大家早上起来黄棉袄一披,冷时再在腰间扎一根绳子,干活热了地头一脱。休息了是凳子,下雨了是雨衣,中午送饭地头小歇又成了午睡的床垫了,打夜班的更是离不开它。这一年四季离不开的物件还不是宝吗?第二年总后又送来了一批部队换下的棉军衣,每人都买了几件,军用黄棉袄不但成了我们长年的“工作服”,就是探亲回乡、进城办事,都一定穿上它。甚至结婚了,新郎倌的礼服都是舍不得穿的那件半新的军棉袄。
黑龙江省各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一看到黄军棉袄就知道是军垦农场的复转官兵。衣服虽旧,那是一个个是要买卧铺的,口袋子里有票子,都是见过世面又懂政策讲道理的,一点都不能小瞧,要是像对待盲流那样随随便便推拉驱赶他们是会有麻烦,要倒霉的。他们为了捍卫复转官兵的尊严不仅会找到站长告状,弄不好还会向上反映,向报纸写信,对百姓吆五喝六惯了举止粗鲁的服务员,不承认错误,不陪礼道歉是过不去的。
黄绿色军棉袄成了我们北大荒军垦战士没有明文规定的“统一着装”,成了军垦战士区别于穿黑棉袄的支边青年和盲流人员的标志,成了我们做 “永不放下枪”战士的北大荒情结。这种对黄军装的感情只有戎马一生的职业军人才体会得到,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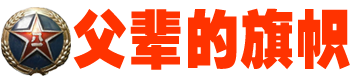 父辈的旗帜
父辈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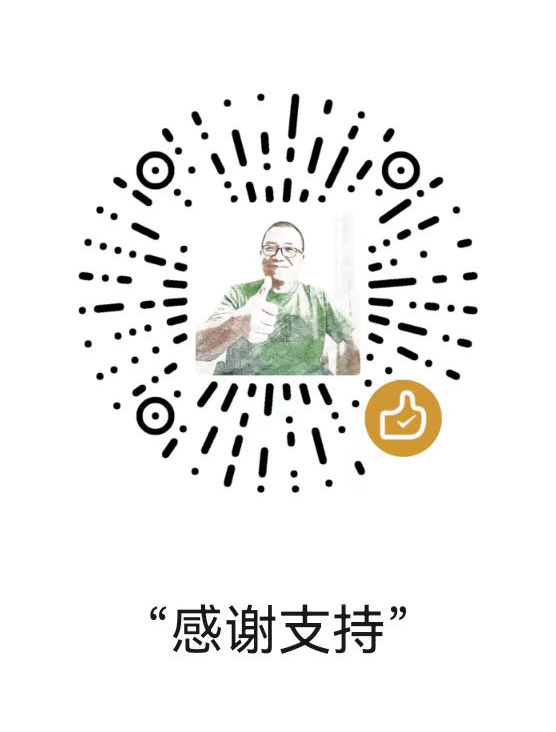


评论前必须登录!
立即登录 注册